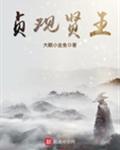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春秋五霸越王勾践吴王 > 第二十三章 会盟舒州(第3页)
第二十三章 会盟舒州(第3页)
伯辛问。
“若把他们一块儿带走,会引起别人的警觉。”
伯辛刚一转身,范蠡又将他叫住:“再带一些吃的穿的,以及五谷和做农活的家什。”
伯辛轻轻颔首。
半个月后,范蠡面谒勾践,辞之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今臣事大王,前则无灭未萌之端,后则无救已倾之祸,致使大王辱于会稽。臣本当立死,然所以不死者,大王之仇未报,越国未兴,臣不敢先死。幸赖宗庙之神灵,大王之威德,以败为成。今不只灭吴,大王又居天下霸主之位,大王倘免臣会稽之罪,愿乞骸骨,老于江湖。”
勾践一脸吃惊地问道:“子说什么?”
范蠡缓缓说道:“臣要辞去大夫,做一闲云野鹤。”
勾践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行,子不能去。”
范蠡道:“臣意已决,大王即使留住臣的人,也留不住臣的心。”
勾践见范蠡去意甚坚,潸然泪下:“寡人赖子之力,才有今日,正要共享富贵,奈何弃寡人而去?留则与子共国,去则妻子为戮!”
范蠡道:“臣固当死,妻子何罪?死生唯王,臣不顾矣。”
勾践道:“子不必如此决绝,寡人给子一天时间。明日此时,还在这里,回寡人的话。”
范蠡稽首而去,挨至黄昏,乘一扁舟,出齐(女)门,涉三江,入渤海湾。至今齐门外有地名蠡口,即范蠡涉三江之道也。
次日,勾践左等右等,不见范蠡来见,忙使人召之,方知范蠡已于昨日子时一刻遁去。勾践愀然色变,谓文种曰:“蠡可追乎?”
文种曰:“蠡有鬼神不测之机,不可追也。”
言毕而出,一道士拦而问曰:“汝是文大夫乎?”
文种颔首。
道士双手呈书,言之曰:“此乃范大夫之书也。”
文种接书,展而阅之。书曰:
弟前言退隐江湖之事,兄不以为然。然弟经过半月的深思,还是觉着你我应该退出江湖。“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夫差之言不谬也。弟观大王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今不去,必为大王所诛。
文种看罢,欲待详问道士,已不知何往矣,喟然叹曰:“少伯之虑,岂不过乎?”
某日,与计倪闲坐,言及范蠡之书,计倪道:“范蠡的话,也许是对的。”
三个月后,勾践起驾还越。也不知是他真的怀念范蠡,抑或别有用意,突然降旨一道,让范蠡之子范江承袭大夫一职,且以百里之地相封。范江勉强就职,但封地坚辞不受。
时隔一月,又命良工,用上等之金,铸一范蠡之像,置之座侧。
对此,文种不仅没有顿悟,反觉着范蠡多疑,不该出走,愧对勾践。
计倪、诸稽郢从中悟出了一些道道,效法范蠡,也来一个退隐江湖。
曳庸也想退隐江湖,不知为甚,勾践竟然没有同意,曳庸便装起疯来,不再上朝。
唯有文种,照常地上朝、下朝。一有闲暇,便去街巷或乡村转悠,遇有贫困之人,施以钱帛。遇耕者,躬身秉耒,朝野皆以为贤,勾践深忌之。
是时,鲁国之君乃是鲁哀公,但真正掌握鲁国大权的是“三桓”
。
何为“三桓”
?
“三桓”
者,鲁国的三家公族公族:诸侯的同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因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所以又称“三桓”
。
“三桓”
的崛起,始于经济,他们不断扩展私田,致使公田公田:指井田制度下,由若干农民共同耕种,而将收获物全部交给统治者的土地。同私田相对而言。,也就是井田数量日益减少。井田少了,国家的收入自然也就少了,入不敷出,不得不实行“初税亩初税亩:中国古代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中国古代征收田赋的开始。”
。这一实行,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收税,这就等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一承认,加快了鲁国井田制的瓦解,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奴隶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井田制一瓦解,奴隶社会自然而然也就瓦解了。故而,各诸侯国的君主,对鲁国很关注,对“三桓”
恨之入骨。作为霸主的勾践,岂能坐视不管!
勾践几次欲要出兵鲁国,讨伐“三桓”
,但他深忌文种之才,以为灭吴之后,无所用之,恐其一旦作乱,无人可制,遂把讨伐“三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