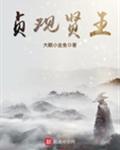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春秋五霸越王勾践吴王 > 第二十三章 会盟舒州(第4页)
第二十三章 会盟舒州(第4页)
之事搁置下来。
“三桓”
呢,得寸进尺,来一个“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他们不只分了公室的土地,还分了公室的军队,致使鲁哀公一无所有。鲁哀公越想越气,唆使“三桓”
的家臣和其他宗族的人起兵反抗“三桓”
,结果全被“三桓”
镇压下去,鲁哀公不得不跑到越国,哭诉于勾践。
这一次,勾践不能不管了。但要出兵鲁国,文种怎么办?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杀!
既然铁了心要杀文种,何患无名?
可他这个“名”
,太勉强了。
是时,文种有疾在家,闻听大王到了,抱疾而迎。勾践登堂之后,解剑而坐,一脸严肃地说道:“寡人有一疑事,百思不得其解,特来向子就教,请子不吝赐教为盼!”
文种慌忙一揖说道:“大王太高看为臣了,为臣不敢……”
“当”
字未曾出口,被勾践摇手止住:“古哲人有言,‘志士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道之不行’。子有七术,寡人行其三,而吴已被灭,尚有四术,安所用之?”
文种开始冒汗了,硬着头皮回道:“臣不知所用也。”
勾践曰:“子如果真的不知,寡人这就告子,余之四术,可为寡人之先王谋于地下!”
言毕,丢下佩剑,升舆而去。
文种跪送勾践下堂,方才起身拿起勾践所遗之剑视之,剑匣有“属镂”
二字,即夫差赐子胥自刎之剑也。
文种仰天叹曰:“古人云,‘大德不报’。吾不听范少伯之言,终为越王所戮,岂非愚哉!”
说毕,泪如雨下。
少顷,忽又大笑:“百世之下,论者以吾配子胥,亦复何恨!”
遂伏剑而死。
勾践得知文种已死,大喜,葬其于卧龙山,后人改其山为种山。
一年后,海水大发,穿山胁,种之冢忽然崩裂,有人见伍子胥同文种前后逐浪而去。今钱塘江上,海潮重叠,前为伍子胥,后乃文种也。
勾践杀了文种,本应出兵鲁国,鲁哀公突然驾崩,遂止。
三个月后,又欲出兵,国内叛乱迭起,叛乱者多为文种、范蠡旧部,闹得勾践疲惫不堪。不得已,遣人去访范蠡,欲让范蠡出山为他收拾残局。
是时的范蠡,早已更名为鸱夷子皮,躲到齐国经商去了。
他之所以要更名为鸱夷子皮,乃因伍子胥而起。
伍子胥的文韬武略,简直是举世无双,为吴国的振兴和强大,立下了不世之功,却被夫差逼死,装入鸱夷之器。
范蠡之所以要更名为鸱夷子皮,一来为了纪念伍子胥,二来也是为了警告自己:你本已该死,却没有死,但过去的辉煌已经不再,你的一切要重新开始。
他几经考察,决定定居蒲谷,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制盐,以盐做物物交换,换得大批廉价的五谷、生丝或漆类物品。而后,再将这些廉价的物品,运往缺少这些物品的地方出售,不到五年,赢利的钱,折合成黄金竟达两万镒,运送物资的帆船有一百多条。对于附近的百姓,凡经济上有困难的,他便施以援手,或一百或一千(青铜块)地施舍。
他的财产,他的贤名,很快传遍了全国。齐平公三次遣使,恳请他担任齐国的相国。
虽说范蠡无意重登政治舞台,但他居住在齐国,对于国君之盛请不能一拒再拒,便把家事和买卖上的事委托给伯辛和范江母子,带上西施、捷鸢、范海和范高,到临淄上任。
三年前,范蠡已经遣人将范江母子偷偷接到了蒲谷。
后经西施力劝,范蠡又将捷鸢收为小妾。
范海为西施所生,范高为捷鸢所生。
当相国不同从商,不能总躲在后台,得上朝,得处理朝政,得不断地见人,包括各国的使者。这一见,便露了馅儿,朝野上下都知道,鸱夷子皮就是范蠡,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谋略家。
于是,越使跟踪而至,拿着勾践的亲笔函,恳请他回越平叛。
范蠡虽说深恨勾践,但他不恨越国,越国在勾践手中已经亡了。是他和文种,再造了一个越国,就像伍子胥把吴国看作他的根、他的儿子一样,范蠡也把越国看作了自己的根、自己的儿子。儿子有难,做父亲的岂能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