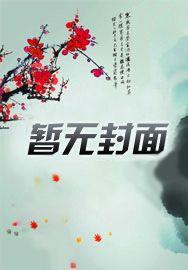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春秋五霸越王勾践吴王 > 第十九章 子贡救鲁(第3页)
第十九章 子贡救鲁(第3页)
夫差正与西施相拥而饮,将头微微一抬说道:“什么事,看把你乐的……”
“越王遣文大夫前来还粟,也许是越地肥沃的缘故,那粟又粗又大,食之,又香又甜。您看……”
一边说,一边将丝包放到夫差面前,打将开来。
“哇!”
西施惊叫一声道,“这粟恁饱满呀,除了臣妾的家乡,别的地方绝对种不出这样的粟来!”
夫差抓了小半把越粟,一边看一边说道:“嗯,这粟不错,收入内府内府:国君内廷的府库。,留作王食。”
伯嚭笑了:“大王,这粟是五万石呀!您吃到猴年马月呀?”
夫差也笑了:“依爱卿说该怎么办?”
伯嚭道:“若依老臣之见,交给内府三百石,余之散与国人,以做粟种。这样一来,明年咱们仓库里的粟,将会翻着跟头往上长,您也可年年吃到精粟了。”
“嗯,这主意不错,就依爱卿所奏吧。”
于是,国人皆以越粟为种,因越粟乃熟粟,能出得了苗吗?没有苗,哪来的粟?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来年,吴民大饥,夫差还傻呵呵地认为,粟苗之不出,是土地的不同,非粟种之过也。
勾践见文种之计得逞,乐得眉开眼笑,商之文种曰:“吴粟绝收,民大饥,寡人欲兴兵伐吴,可乎?”
文种道:“吴粟虽说绝收,军中尚有陈粟。此时伐吴,顶多打个平手,不如再等一等。”
勾践不甘心,又召范蠡进宫。范蠡曰:“文大夫之言是也。”
勾践道:“是攻战之具尚未备乎?”
范蠡对曰:“非也。”
勾践又道:“是卒不精乎?”
范蠡对曰:“非也。”
勾践道:“吴民大饥,吾之攻战之具已备,卒又精,为什么只能打个平手?”
范蠡对曰:“其因有二。伍子胥未死,一也;吴之师,就兵员来说,为我四倍,又是百战之师,二也。”
勾践轻叹一声道:“诚如爱卿所言,这吴何时才能伐呀?”
范蠡对曰:“必等伍子胥死后。”
“他要是不死呢?”
“臣有办法让他死。”
“既然这样,爱卿快快让他死吧!”
勾践有些迫不及待了。
范蠡道:“即使伍子胥死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能打败吴国。”
“为什么?”
“臣已经说过,就兵员来说,吴师是我四倍,又是百战之师,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诚如爱卿所言,这吴还怎么伐?”
勾践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创造条件呀!”
“怎么创?”
“想办法削弱吴国的国力。”
“怎么削?”
“夫差自攻破咱国之后,雄心勃起,意欲称霸天下。咱就让西施给他吹枕头风,怂恿他对外用兵。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只要他对外用兵,不可能不死人,不可能不消耗粮草钱帛。人死得多了,粮草钱帛消耗得多了,国力自然就会削弱。”
勾践脸上现出了少有的笑意:“好,这办法好。有劳爱卿亲去吴国一趟。”
范蠡道:“臣遵旨。”
翌日,范蠡带着易了容的南林剑女,并虎皮一张、狐皮两张、葛布千匹,前往吴国。范蠡在吴住了三天,返国的时候,把南林剑女留了下来。
范蠡刚刚离开吴国,鲁国使者子贡,骑着一头骡子来到了吴都姑苏。子贡者,卫国人,名赐,孔子高足也。孔子带着子贡等人周游列国,不为列国所用,返国后,一边教书,一边删述《诗》《书》。一日,学生子张自齐至鲁,来见其师。孔子问及齐国之事,子张对曰:“齐国国君,怕是要易姓了。”
孔子惊问:“易之何姓?”
子张对曰:“陈姓。”
孔子问:“是齐相陈桓吗?”
子张对曰:“正是。”
说起这个陈桓,孔子并不陌生。陈桓的先祖,原来姓田,叫田敬仲,陈国人,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田敬仲逃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工正:官名。春秋时,齐、鲁、宋、楚等国设置,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改姓陈,广结人缘。以大斗(田家的量器)出贷,以小斗(公家的量器)收的办法,收买人心。
是时,齐国的粮器有五种:升、豆、区、釜、钟。四升为豆,由豆至釜也是四进位制,釜至钟是十进位制。田家的斗、豆、区、釜等四种量器,比国家的大了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