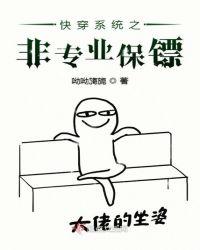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珠颈斑鸠筑巢指南by嫉妒怪物 > 第82章(第1页)
第82章(第1页)
几鸟不由得更严肃,却也变得更沉默了。
“深哥……”
像是知道自己现在不容乐观,朱树也没有再把精力放在其他的上面,而是继续扭头看向朱云深。“深哥,你可以,再喊一遍,我的,名字吗?”
朱云深又往朱树的方向走近几步,减去了两鸟之间所有的距离,随后用很轻很柔和的声音喊了一句:“小树。”
“嗯。”
朱树低应道,接着挪动自己沉重的身体,像刚破壳的雏鸟一般贴向教会他成长的兄长,又用尽此生最后的力气念了一声:“哥。”
尾音落下的几秒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一只叫做朱树的红隼。
===
三隼一斑鸠带着那条将死的中介蝮和朱树的尸体回到了昨夜暂歇的地方,仿佛是某种天生的默契,其他的红隼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回到了那里。
他们看着闭目的朱树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或许无声地悲伤了一个世纪。
随后以朱海为首,几只红隼一个接着一个地仰着头发出凄厉的叫声,声音在寥无人烟的野外回荡,从秦淮之北飘向秦淮以南、从现在传递到过去、从此处流淌向生灵魂归的地方。
安葬之前,朱云深拆下了一根朱树的尾羽,又找了些柔韧的草茎搓成细绳,而后把尾羽绑着挂在了脖子上。
他说,朱树喜欢南方越冬地,一直把那里当做自己的第一家乡,他没有办法把朱树的躯体带回去,那就把这跟尾羽当做替代品,希望朱树的魂灵能够顺着羽毛回到他喜爱的地方。
又说,迁徙之路还没有走完,剩下的风景他应该要带着朱树一起去看。
还说,鸟的一生能记得的东西不多,他怕自己会逐渐地忘记朱树的模样,所以以此提醒自己去记得。
朱云深说了很多,但安澄知道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或许只有很少——他很难过,他舍不得。
众隼将朱树安葬在最高最粗壮的树下,朱海说他是在大树底下重生的孩子,最后也应该回归到大树的怀中。
由此这棵独自林立了多年的树旁,多了一个小小的山包,也多了一只陪伴它的鸟。
安葬好朱树之后,那条将死的中介蝮就成了众鸟发泄愤怒和悲伤的唯一途径。
被利爪刺透皮肤、毒液超量分泌、从高处摔落到石碓中……前面种种已经让中介蝮虚弱不堪,现在众鸟更是不会手下留情,他们几乎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扒皮抽筋,而毫无还手之力的中介蝮只能在意识还算清醒地时候忍受无边的疼痛与折磨、一点点地感受到自己的死亡。
等他成了一堆看不出模样的肉泥时,众鸟才堪堪停手。
但这个时候,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即刻迁徙的动力了,只能守在安葬朱树的大树旁又歇息了一天。
等到了寻常晚间入睡的点,还是没有一只红隼闭眼,可他们又纷纷心思各异地沉默着,氛围一片死寂。
等熬到月亮高挂、却他们之外的万物都陷入沉睡的时候,原本直站着的朱云深突然扇动翅膀离开了枝桠。
安澄想了想,感觉朱云深的状态不是很对,就还是自作主张地跟了上去。
朱云深一路飞行,最后窝在了朱树的小小墓包旁,很沉默地抬头看着月亮。
安澄到来的一瞬间他就发现了,不过还是没有说什么,甚至还十分贴心地让出一个位置来。
“大人,你没事吧?”
安澄靠近他低声问着,实际自己的心也很空。
朱云深没有立刻回答,拧着头盯着墓包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又将脑袋慢慢转正的时候,他才开口:“我被人类养了一年,等那个人类死之后,我才回到的集群。”
声音很低很缓,没有刻意讲故事,只像是在抒发什么。“朱树是我回去之后遇见的第一只雏鸟,他不会飞、不会捕猎,摔在大树下动也不敢动。”
后来的故事也无需多说,听的鸟能够自动补全。
“父母死后,就由我和大哥将他们往南方越冬地带,当时我们也路过了这里。”
“就是那个时候和那条中介蝮结下的仇,他冬眠之前想要再吃一顿饱饭,把主意打在了我们的身上,当时还瘦瘦小小的朱山险些被吃掉。”
回忆到这里,朱云深的语气变得轻快些许,眼中似乎带上了很淡的笑意。“他脑袋上的羽毛被弄坏了些,再长出来竟然变成了黑色的,还伤心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安澄想到朱山的癞子头,也笑了,没想到竟然是这样来的。
说完这些,朱云深又陷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垂头啄了啄身上挂着的尾羽,低声说:“没想到一年过去,他身上的羽毛就这样长了。”
一年过去了,才过去了一年。
被暗地里造谣了怎么办?
黄茅很自然而然地成为集群当中的一员,在整装重发的那一天就跟着他们迈上了往东北而去的迁徙之路。
朱树的事情没有隼再提,这仿佛成为了一道化脓但结痂了的伤口,虽然仍在暗自溃败,可不去主动触碰就不会有那么疼痛,日子久了之后,众鸟又权当那道伤疤已经悄然痊愈,不会再产生二次病变——至于这样做是真是假是否有用,短时间内也无鸟有气力去考究。
总之,大约在事情发生的一周后,他们就生活就被强行地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或许还算快乐。
中午休息的时间。
“大人,所以现在那黄茅和朱川就已经是伴侣关系了吗?”
安澄的喙一张一合,虽然吞咽的是黄茅为了讨好而上供的食物,但还是非常没有道德素质地在背后偷偷地跟朱云深蛐蛐他。“但我看着怎么好像不太像啊,感觉还是黄茅在倒追朱川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