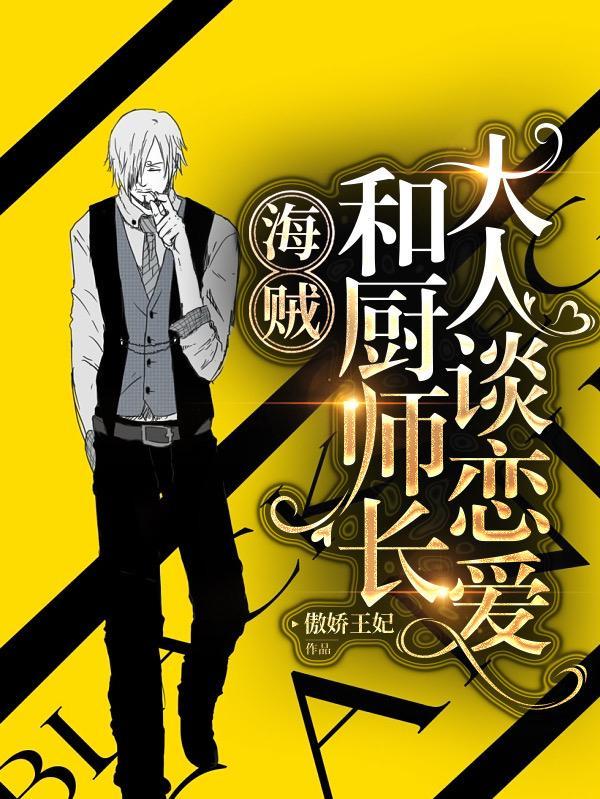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悠然种田养包悠然种田养包子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软红有些疑惑地凑近小丫头背上一闻,惊讶地问道:“好香,你这背上?”
满菊冷不丁地想起了那香艳的梦中,手上盈盈满握的软香,一身鸡皮都瞬时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解释:“呃,我,我涂了自家的土药,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治跌打损伤的外症倒是极为对路。”
说着,拿出了那个小木盒装的绿糊膏。
既然自己不想皮肉多吃苦,伤好得快也瞒不过人,反正这伤药在谢琚那里过了明路,身上还有余货也说得通。反手给自己后背上药非常麻烦,不如请软红帮忙上药,满菊也正想拿这小药膏谢谢她的热心。
软红挑了点药泥在鼻端一闻,细眯双眼,悠扬长叹:“真正好药,异香更是——难得呀!”
说着扑哧一笑,又挑起一坨绿糊往满菊背上擦去,几下涂抹后,更是满室生香,她兴致大起,问:“惜福,这药旧伤可有用?”
“应当也有效吧?”
满菊真不太确定。
“若是这药有多,你帮我也抹些,成不?”
软红侧过头,在小丫头耳边柔声问。
“多,多,多多……”
这一贴身近话,满菊立时又结巴了,耳根通红好容易吐出整句话:“多得很,正想拿这小玩意谢谢姐姐呢!”
这可把软红笑得腰肢软摇,波涛汹涌,半晌才止住笑,她倒有股子光棍泼辣劲,刷地就敞开衣怀,弓腰坦背,将一片莹白的背肌全数裸在满菊眼前,道:“背上多,腿上也有,劳烦你了,小丫头。”
满菊正被这突然闪在眼前的一大片白花花好肉差点给晃瞎眼,听她一说才注意到软红背上白净的皮肉上满是密密交织的鞭痕,有新有旧,深的已呈黑紫色,狰狞入骨,浅的也入肉三分,艳丽的血色衬着雪白的肌肤,格外有种凄烈的美感。
“你,你这是……”
满菊大惊,难道谢琚这家伙真有不可为人知的s-癖好?
“吕大小姐的鞭子,莫非你没挨过?”
软红笑嘻嘻地扭过头问。
“可也没这般……”
原来是母老虎干的,可是吕嫣没事打谢琚房里的人干什么?
软红上下打量了一番小丫头,挺了挺盈盈丰胸,意有所指地长叹道:“你自是不能和我这般人才比的。”
满菊被她说得脸部抽筋,不知该摆上愤怒、惊叹、同情还是无奈的表情好,这女流氓既如此想得开,她倒也不便再多问。
“咱们做人奴婢的,便是贱如草芥,贵人开心要了你的身子是你的福份,贵人不开心把你碾成泥,难道还有你说话的份?”
见她不问,软红也不笑了,冷哼一声,道:“快帮我涂药罢。”
满菊一时无语,应声挑起药膏,细细地在她背上新伤旧痕之处涂抹开来。
闷闷地沉默片刻后,软红大约也有些耐不住,开口娇声软气地悄悄说起了公子和大小姐的八卦。
据她说来,谢琚谢二公子与吕嫣吕大小姐早有婚约。
谢家公子爷那也是有身份的主,是中原谢家的嫡次子,什么?没听说过谢家?华朝时名动天下的谢灵妃总听过吧?什么,还是没听过?哧,乡野鄙陋的小丫头片子!总之谢氏是贵阀名门,泱泱大族,传承可不止几百年了。虽因改朝换代元气大伤,却也不是一般土豪可比。
吕家么,虽是以武晋身,新朝新贵,可连皇帝都说过“欲与吕共天下”
,权势彪炳,富可敌国,两家也称得上门当户对。谢公子虽非嫡长子,不能传承家业,但人才出色,又有祖荫,待其兄继位后,请皇帝赐个官爵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可不知吕大小姐拗的什么劲,眼见十六花信将过,死活就是拖着不肯嫁。谢琚借住于吕家,名义上自是世谊交好,借居读书,可私下里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吕大小姐不肯嫁,婚事又绝不可能作罢,谢琚那等世家公子都是十一二岁就开荤的,总不成让男人吃素等她。
哪怕吕家家风承自秦时贵胄,女儿贵重且风俗彪悍,婚前若是有喜爱的男子,邀歌一曲便可入帐而欢,可如今久居中原,也不敢再如此放纵女儿。说不得还得给委屈了的准女婿送上各色美人,让他把委屈咽到肚子里,免得坏了吕家贵女的名声。
只是女人这种生物都有一种通病,自己的东西,哪怕再不喜欢,可要时不时让别人舔上一口半口的,这恶心劲也够瞧。不能打谢公子,侍过寝的奴婢就只好成了吕大小姐的出气桶筒。
“……你当清尘一副人间仙子的模样,她身上又有几块好皮肉?”
末了,软红冷冷地哼了声,其意未尽,其恨难吐。
☆、识字录方
听了一肚子八卦,满菊差点憋笑出内伤,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啊!黑心小白脸遇上爬墙母老虎,真是一场闹剧,怪不得初见这位公子爷时,这位一付别人欠他八百两的要债脸。只是八卦听过便罢,为奴为婢、忍声吞气的日子还得照过,连嘲笑两声都得憋在肚子里,免得让人知道告上一状,又得皮肉开花。
小还丹那坑爹的强大春-药副作用被挖掘出来后,满菊也考虑过是否给公子的菜里边下上个十七八颗的,让这沙猪男精尽人亡算了!只是一来小还丹这奇怪的副效也不知是哪几种药偶然配合触发的,想单独分出纯粹的春-药可能性几乎为零,要是不分离副效整个让谢琚吃——按小还丹那理气壮体的主效,极大的可能性是内伤药变成了壮阳药,到时候被折腾死的就该是软红清尘她们了。
说不定小白脸见这突如其来的“能力”
如此威武,不分清红皂白,就给她这个身世有疑、会制点古怪药品、疑似怀恨在心、又能接触到公子饮食的厨房工作人员一顿好打——这次该逼问壮阳药的配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