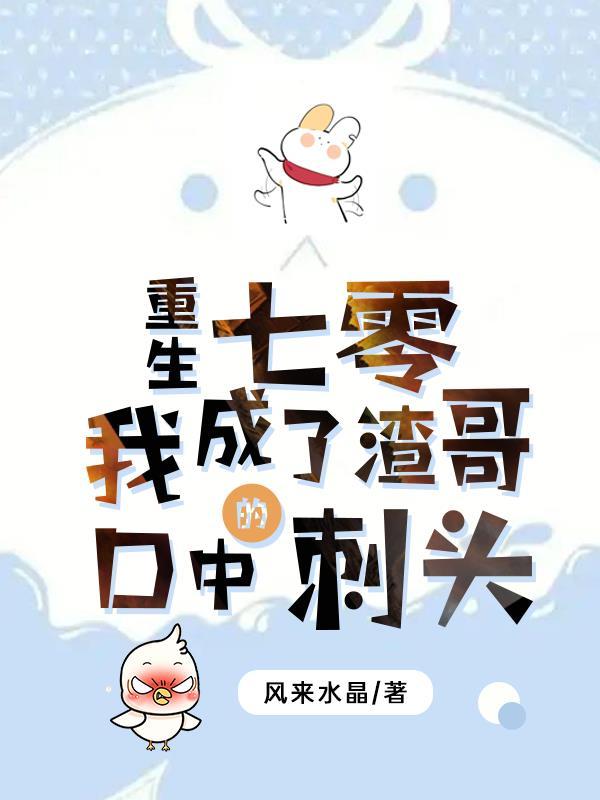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贵女谋权55章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戚言敛起笑容,冷哼一声:“说得甚么话。”
襄君何曾是羊,王姬又何曾是虎呢?
不过是沾了天子的权欲,本该荣耀一国的王姬婚事,却成了谁都不想碰的烫手山芋。
但此事之于襄国,又与靖国不同。
靖乃万乘大国,一方霸主,就连僭越称王之事都早已干过,违抗王命便也抗了。
不要说靖王真情实感地演上了这么一出,即便是不演,靖说不娶,王室又能奈他何?
可襄国毕竟贫弱许多,真要叫板王室,未免气弱,再有个不敬之罪,被哪家邻国揪了错处,料理不好,恐怕又得是个灭顶之灾。
眼下不止闵煜忧心,就连戚言也目露沉思。
戚相食指在桌案上轻敲着:“国君待我想想,实在不行……”
她的声音低沉下去,未尽之言消失在唇齿间。
闵煜不知她未出口的那半句话究竟是什么,只觉得嗅到一丝不平常,似乎极为大逆不道,不至万不得已,绝不动用。
只是事情的转折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使者接了新的天子令,正要动身前往襄国。
可一道新的密令紧追而来,将那诏令追回了。
与此同时,王畿传出天子驾崩的消息。
“王姬怀抱幼子登基,代为听政。”
戚言阅完竹简,将它投入火盆,缓缓烧去。
此时已过了春祭,四处的积雪都开始逐渐消融,只是戚言一贯畏寒,是以炭火未歇。
这大约是戚府上唯一称得上奢侈的东西了。
貍奴也喜暖畏寒,与她一同缩在屋子里,全然不顾主人正在忙于天大的正事,娇气地往她怀里钻。
戚言也纵容它,放任这团毛绒在她怀中寻摸好位置,舒服地窝起来。
轻手抚摸那身柔软皮毛,猫儿喉间便“咕噜咕噜”
地发出餮足的声音。
襄君一如既往地坐在桌案的另一边,目光也自然而然落向那貍奴,口中却记挂着王畿:“天子年富力强,正值春秋鼎盛的年纪,怎么消息来得这么突然。”
戚言笑:“是啊,怎的如此突然。”
大约是有人终于忍无可忍了吧。
她叹息:“王姬竟是个有趣的人。”
闵煜闻言点头:“临危受命,确实心有丘壑。”
如今王室衰微,天子驾崩得早,膝下唯有一子,尚且婴幼。内有豺狼,外有虎豹,要靠一己之力撑起门庭,恐怕大不容易。
戚言望着他,眼中意味深长:“天子既崩,使者来报后,诸侯自当前往奔丧,此番我与国君同往。”
初遇
既为天子奔丧,诸侯仪制必要齐全,车马行路缓慢,要走两个多月方可到达王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