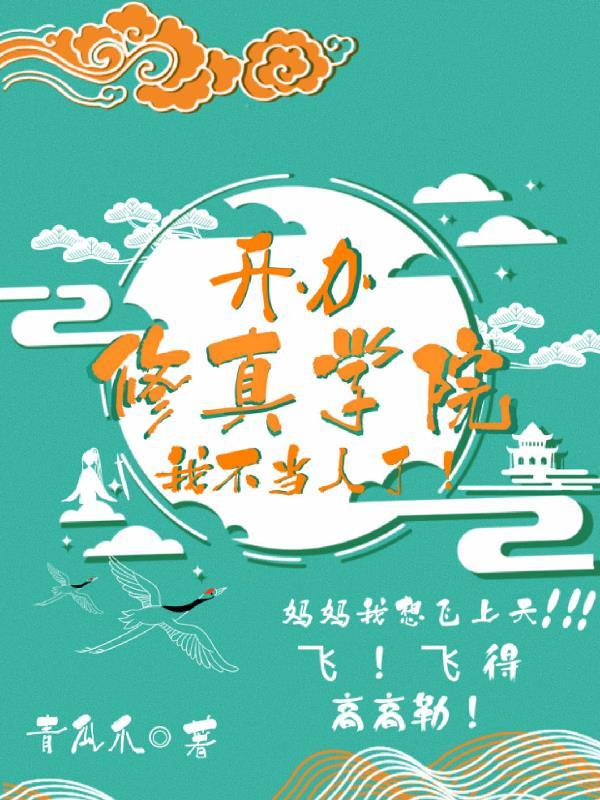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局部降雨by > 第97章(第1页)
第97章(第1页)
林平愣怔着,视线黏在镜面,他入了迷,丢了魂,急不可耐的扭头,窦利钧薄唇迎上来,浴室回蕩起耻人的声响。
“我让你丢人吗?”
窦利钧问。
林平摇头,铜扣敲在瓷台上,啪嗒一声。
“那为什麽不承认我的身份?”
窦利钧抱着他,下巴杵在他脖子窝,低低的问:“老婆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林平不去管他是不是喝醉了,急于否认道:“不是!我没有。”
窦利钧宽阔的肩膀拢着他,镜面里,被美化过的,一览无余之中,他在窦利钧怀里竟显得不那麽精健,反而被抱笼的让他自己都不大敢认。怎麽是那个样子的,林平眼神闪躲,否认那个又羞又嗔的人是自己。
“我是你的谁?”
窦利钧掐着他下巴,逼他直视那面镜子。
林平不算瘦削,他的肌肉线条是起伏的,明朗的。腿也瘦不成杆儿,合起时没有那麽大的空隙。
“老公。”
林平从喉咙挤出这两个字。很热,又烫,他被迫前倾,一只手按在雪白的墙上以做支撑。
“嗯。”
窦利钧薄薄的手掌盖在他手上,指缝交缠,亲密无间。“下次,会在别人面前承认我是你男人吗?”
镜旁的柜台上摆放的剃须刀颤两下,彷佛经历了一场地动山摇,它颤巍的,最终倒下。林平以前用老式的剃须刀刀片给他刮胡青,他像是皮薄,冷不丁就会划出血,后面就换了电动剃须刀。剃须刀刀身有道弧,林平那只手就在柜台下,短短的指甲扣的墙上有了划痕,剃须刀躺立两秒,被震下柜台,摔成两瓣,首尾分离。
林平来不及去看,就被窦利钧掐着直视明晃晃的镜子,他腿弯禁不住的抖。窦利钧覆盖他,用低沉的嗓音勾缠他:“会吗?不会我们就练习,一直练习到老婆会说这句话好不好。”
“会。”
林平哆嗦着,知他这样分明就是没醉,憋了一路,要听自己说:“你是我的男人。”
皮带铜扣浸在管道旁的水渍中,黑色西裤湿了也不太明显,堆叠着,深深浅浅。早上林平还有打扫这里,他怕湿滑的地面会导致人不小心摔跤,到了晚上这里就开始积水,可能是窦利钧开水龙头了吧。
眼下他已无暇顾及,灯光忽远忽近的折射在光滑镜面,他在晃动中被芒刺一般的冷锐的光线照透。墙面的光膜漆被他抠出月牙似的印子,而窦利钧是始作俑者。
过程中,林平不小心碰掉他一瓶香水,浓浓的香根草味道在浴室爆裂开,馥郁的味道令林平有些喘不过气。嗅到鼻间的恍惚都是窦利钧的味道。
他要是知道那瓶香水的价格他就不会跟着窦利钧胡闹了。
他拿扫帚收拾玻璃残渣,窦利钧伸手,他不放心道:“等下割破手。”
窦利钧被他勒令站的远远的,看他弓腰打扫卫生,他真能干,窦利钧不知不觉又走到他身后,他说:“我再给你买一瓶吧。”
“不用。”
窦利钧哄他,“给你摔着玩儿。”
林平嘟囔了他一句毛病,处理掉垃圾后想起什麽,死盯着窦利钧不放。窦利钧本来在沙发上看电视,被他看的默默转过头,四目相接。林平不躲,目光沉甸甸的,窦利钧不动声色的问:“怎麽,你想再来一回?”
林平摇头,说:“张与加在用的那个味道,你给他挑的?”
窦利钧嗯了声,又转回去看电视了,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也没往深处想。他不以为然的恰恰是林平在意的。
“你觉得…我适合用什麽。”
林平问出这句话时手指差点没把裤缝给抓出线头,他不习惯身上有味道,总是尽可能的保持干爽。他也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不实际的东西。可他问了。他清楚明了的知道他不是要买要用,他只是想知道…窦利钧是怎麽看他的。张与加用着温吞矫软的味道,是不是代表他在窦利钧心中就是那个样子呢。林平突然很在意窦利钧的看法,他怕窦利钧说出一个不好的词语,就像,就像韩元就点评他粗人一个一样,哪怕是以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他心里也会很不好受。
窦利钧故作沉吟,林平等他片刻,见他不语言,逐渐感到低落。
窦利钧适时凑到他耳边,呵出一股热流,“你适合用老公的。”
林平鼓胀的心像一颗气球,满了以后,几乎要炸开。窦利钧不要脸,他撇开头,不看窦利钧。窦利钧不是非要逗到他脸红,正色道:“我说不出来,因为我喜欢你,我觉得你用什麽都好。”
那天的窦利钧不知道是不是被酒精蚕食掉了些许精明,他竟没往深处想,林平在吃醋。如果他能反应过来,就会抓着这点不放,他握的筹码越多,内心的偏执便会越少。
第一声蝉鸣炸开时,林平带窦利钧跟林顺一起吃了个饭,在大学附近,一家小餐馆。林平带了他给林顺买的鞋,林顺收到以后很开心,道了两句谢,目光挪到窦利钧身上。窦利钧端坐着不说话,他在外面是这样的,林平习惯了。介绍窦利钧给林顺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林顺是小辈,哪怕只是普通朋友,吃个饭也没什麽。
林平说:“叫哥。”
窦利钧倒不怎麽见林平这幅兄长的做派,他暗暗打量林平,林平在林顺跟前也是家长,林顺看上去很尊重林平的样子。他心痒痒的,觉得林平很会管弟弟,也很会管老公。
“哥。”
林顺沖窦利钧叫。
窦利钧点头,林平抓起他的手,给林顺看他手上的戒指。他俩戴的不是对戒,劳得林平开口,大大方方的一句:“得叫哥,我们俩在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