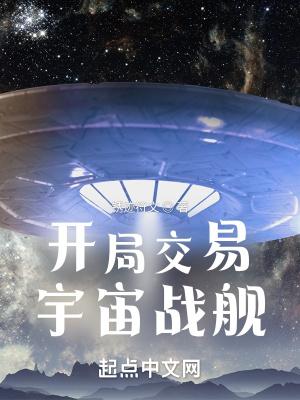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陈米麒个人资料图片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然而当我事后回想,我却觉得他只是习惯了。习惯当一只随时能被人踩死的蝼蚁,习惯当一把被人利用的刀刃,所以他才能面不改色地接受我的审讯。
而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情绪失控,竟然还是因为我向他提起反侦查手段,试图诋毁他阿弟,也就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想,他那句话的完整意思应该是:“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自己。”
那次重逢后,我并没有再接着去他家。因为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水平与生活条件都相差甚远,所以即便我对他多了一层所谓的童年滤镜,也无法快速填满我与他之间那条名为阶级的鸿沟。
转折发生在98年的7月份,当时我外出走访一个诈骗案的受害人,而受害人刚好就在天心供销社工作。
我的意思是,我亲眼目睹了那五个曾经在中学时期共同霸凌过我的人,正在用他们自认为优越的工作与身份对我哥实施霸凌。
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想上前制止,但后背上被他们用香烟烫出来的那一个个窟窿像根根捆绑住我手脚的丝线一般,拉扯着我让我始终无法再动弹分毫。
最终,我成了那场戏里冷漠的看客。
也是在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从被霸凌者变成霸凌者。因为利益,因为需要,因为害怕。
不过说来可笑,在翻阅了老孔带来的调查资料后我才知道,他们居然从来、从来、从来都不曾记得对我做过些什么。
同样的,自那日起,我开始了与陈米的频繁往来。
正如陈米所说的那样,每次去看他我都是等到快凌晨才去,又趁着天刚蒙蒙亮没什么人出来劳作的时候返回,说句难听点的话,这看起来像是在偷情。
他曾问过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只说是在单位上班,还时常漫不经意地借着替他讲解电视剧剧情做幌子向他科普一些刑侦知识。
一个充足的作案动机仅是前提。
自此之后,不知是出于弥补内心的愧疚还是不安,我就经常将那些我自认为他可能会想要或者未来可能需要用到的东西送给他,慢慢的,他那本就不算宽敞的屋子变得愈加拥挤。
那会我还以为只有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想到在陈米面前的我其实是一片肉色的,我把野心与目的统统刻在脸上,身上以及我的血液里,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将这些东西赤裸裸地展示给他看。
可是感情,感情向来由不得人操控。
陈米那有些笨拙的真诚与聆听在一点点地击溃我丑陋不堪的心脏,我有想过终止,但背上的疤痕在天热时总是痛痒,不管我涂多少药膏都无济于事。
99年10月13号,那晚的天气异常闷热,是台风来临的前兆。
我却玩心四起,就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和铁风扇转动的呼呼声,拉起陈米的手就在院子里跳起了迪斯科。许是邓丽君的歌声太过婉转温柔,暧昧的气氛随着我和陈米停下来休息的空档在那间小破屋里到处乱撞。
屋子很小,很快就被它挤满,我和陈米无处落脚,最后只能拥抱着彼此。
我们从过去讲到现在,又从现在讲到将来,再从我很想你讲到搭伙过日子。
然后,我亲了陈米,蜻蜓点水,但我就是亲了。
他是个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很多事情也就都顺理成章了。
我们这两副身体在那张窄小的木板床上交迭,喘息,纠缠。我贴着他,感受着他的心跳体温,我记得他的身体很热,足够将在那上面的我融化到直至被他吞没。
而我,是心甘情愿的。
“你怕吗?”
我问他。
他用身体的颤抖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又问他:“哥,你疼不疼?”
他转过头,两只手抱住我,我像个孩子一样被他抱在他怀里,他的声音低到近乎耳语:“不疼。阿弟很好,哥不疼。”
我想放弃了。我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可很快的,他发现了我后背的凸起,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这是什么?”
我只说是小时候淘气弄伤的。
那一两个月,是我和他自重逢以来相处得最没有心理负担的时光。
我教他识更多的字,还教他写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李哲,哲是哲学的哲。我说我的养父母很疼我,愿意顺着我的心意取名“折”
,但是后来他们说这个字寓意不好,就改成了现在的“哲”
字,意为希望我长大后会是个博学的人。
他就在一旁附和着说:“这个名字好,阿弟真有文化。”
有一次,他还破天荒地问我:“以后我想阿弟了怎么办?”
起初我并没发觉这句话有什么不妥,还特别不害臊地将一个避孕套套在自己的中指,打趣他说:“这样想。”
他的脸登时就红得和家家户户门外挂着的红灯笼一样。
然好景不长,抑或该说命运本就如此。在99年年末得知自己将于2000年年中调至市局刑侦一支队担任副支队长,急功近利的我理智再度战胜了感性。
那个夜晚,我抽着他买的雄狮香烟,他抽着我带来的南洋红双喜香烟。
烟雾弥漫,我看不真切他的脸,只能听到他重重的呼吸声。我探出手想确认他是否还坐在我身边,却被他一把抓住,愣神之际,他将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脸上。
我感受到他脸上的温度,香烟上的火苗也随之熄灭,我又看到了他的脸,由模糊到清晰到再次模糊。
身影又一次起起伏伏。他很顺从,我思绪复杂,这次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仿佛在提前演练一场静默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