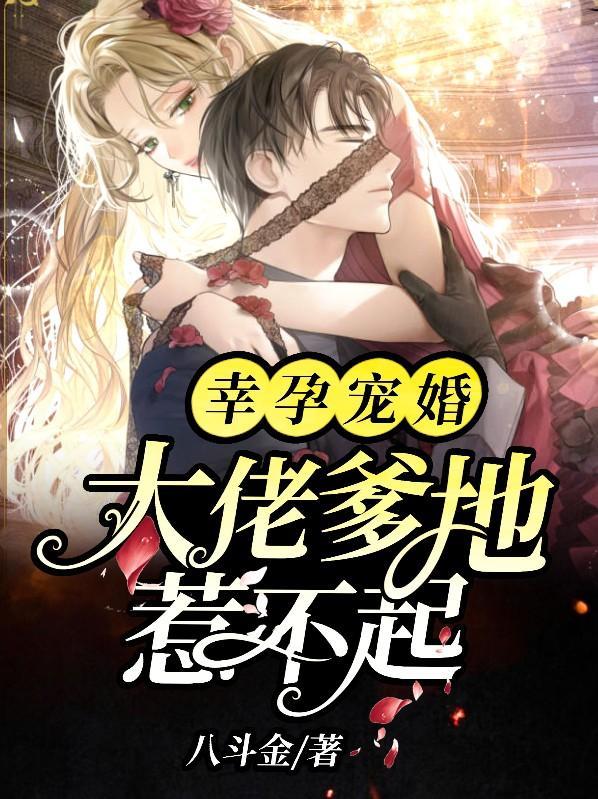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带着红楼到红楼 > 第109頁(第1页)
第109頁(第1页)
他們家在揚州城裡也有別院,庶出的大姑娘還嫁到了鹽商吳家,如此明目張胆的政商勾結,也就甄家能做出這種事。
甄家的其他姑娘還好,都是知書達理,溫柔隨和的性子,讓人頭疼的是甄家的鳳凰蛋甄寶玉。
仗著甄家老太太的寵愛,他總喜歡在內眷裡面私混,尤愛對各家姑娘伏低做小,要是有誰看著不像話想遠離他,他就做痴做狂的鬧起來,像有人把他怎麼樣了似的。
甄老太太豈是個講理的,每當遇到這種事都會倒打一耙毀人名聲,穆月輝在最後著重提醒黛玉,千萬千萬要離這個甄寶玉遠遠的。
黛玉輕嘆一聲合上信,要不是好友提醒,她都忘了紅樓原著中還有個跟假玉齊名的真玉,如今看來這甄寶玉竟比賈寶玉可惡十倍不止,甄家也不是早已失勢的賈家可比,還真是難辦啊。
還有那個甄應嘉,有他在,自家爹爹這個蘭台寺大夫就顯得有些尷尬了,同為御史,卻要低人家一級,雖有個一等男爵位,又如何能跟皇子的外家相比。
爹爹隸屬於都察院,人家卻能直達天聽,在各方面都處於碾壓自家的地位,如今就要看聖上如何處置利用美婢滲透各家的三皇子了。
皇上要是一心維持局勢穩定,輕輕揭過此事,只會更加助長甄家的氣焰,江南政局被這種人處處轄制,爹爹想大展拳腳是沒可能了。
原著中甄家雖然被抄了,也是在林海身故幾年以後的事,顯然即便三皇子被處置,聖上也沒有動甄家的打算,親親老爹還是得在甄家的陰影下憋屈到離任為止。
黛玉正尋思著揚州的事,又有管事來報說佛堂里的女尼已經送去了城外庵堂,問姑娘如何收拾那個院子。
想到堂中的木雕塑像不知見過多少骯髒事,黛玉心裡直泛膈應,讓人把所有東西都搬到西路的禁院去,清掃了留待日後再布置。
管事去後,又有外院嬤嬤來報衙門裡發生的事,聽說鹽農送來了帳本,林生已經親自送人回去了。
黛玉感嘆林生叔的俠義心腸,又擔心鹽農住得太遠,天黑關城門前他回不來,便安排人帶著暖爐和厚衣服駕車去迎,要是趕不上關城門,在外住宿時也能暖和些。
林海自接了鹽農的帳本,就知道接下來會有一場硬仗要打,他剛想回到後堂細細研究,就聽到後頭乾嚎聲響成一片。
林福跑過去詢問,沒多時就囧著臉回來了,上任曹大人因痰癰之症,掛了。
林海也傻眼了,雖說曹大人在他來以前就要死不活的,可好歹也挺了這麼久,怎麼說沒就沒了?
死在前後任交接的時候,是算卒於任上,還是卸任後亡故,二者的待遇千差萬別,這要如何判定?
林海讓曹家人收斂屍身,挪出衙門後堂,而後招集來衙門內的所有官員,商討曹大人之死應該如何定性。
最終大家決定還是給曹家人行個方便,定為卒於任上好了,好歹能多拿些撫恤金,也算大家共事一場的情分。
鹽運使衙門在接近傍晚時發出訃告,沒到一個時辰上任鹽政曹大人掛掉的事就傳遍了揚州城。
對於鹽商來說,馬上就要卸任的上官毫無價值,只打發下人封張銀票就完事了。
他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林海身上,由吳劉兩家起頭,晚膳時眾多鹽商聚在邀芳閣,商議如何給上官添堵。
林海接下鹽農的帳本,對鹽商來說無異於開戰信號,他們之所以不肯付清購鹽費用,為的不是那幾兩銀子,是要以此來要挾上官,占據主導權。
本朝規定,鹽商販鹽必須持有鹽運使衙門發放的鹽引,否則就是私鹽販子,一經發現人頭就要不保。
即便拿到了鹽引,每年覆核一次也讓鹽商苦不堪言,因此才想出用剋扣鹽農的方式來轄製鹽政官員。
官員要是對鹽農的遭遇置之不理,下層的不滿情緒就會集中在官府身上,鹽政官員又不敢對背景強大的鹽商太過分,想安撫鹽農就要在他們面前矮上一頭,以此來達到雙方的勢力平衡。
不過林海跟前面幾任鹽政不同,他出身功勳階層,自身也有爵位,還是聖上欽點的官員,想以背景強行壓服是不可能了。
他要是站在鹽農那邊強行追債,無論是主動低頭服軟,還是被打壓到抬不起頭,都不是他們想看到的結果,想要繼續占據上風,就要商量出萬全的對策才行。
吳劉兩家把眾多鹽商當家請到邀芳閣,共同商討如何度過難關,一群人美人在懷,酒沒少喝,到最後也沒想出如何對付林海,只好先下帖子,把人請出來試探一二,之後再做定奪。
林海料理過曹大人的後事,很晚才下衙回家,讓人在大門口放幾個火盆,跨一遍去悔氣,又讓人傳話給黛玉,這兩天他都要睡在外院書房,不想把霉運傳到內宅里。
黛玉心說爹爹總把子不語怪力亂神掛在嘴邊,到頭來卻比誰都迷信,遠在濟南府時就聽說曹大人快不行了,他能挺到現在已經很給面子了。
既然老爹不肯進內院,黛玉就命人再點幾隻蠟燭,在燈下把穆月輝送來的揚州官員內眷名冊謄抄一遍。
好友是信任她,才會在信上吐槽畫黑叉,被外人看到了可不得了,抄完後黛玉讓人送去前頭給爹爹,把原件直接丟進火盆,讓其完全消失才最安全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