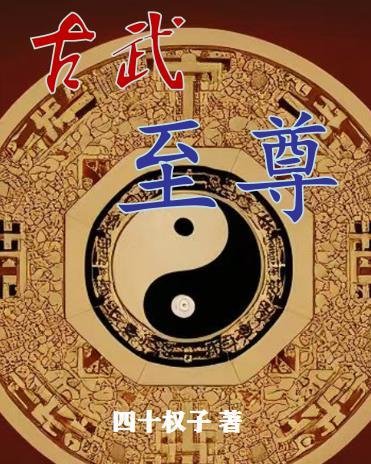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温暖处处充满 > 第31頁(第1页)
第31頁(第1页)
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樣,挑選了貨品從鹽城回來。那次我選的樣式都已經記不清了——我一直在刻意遺忘那件事,即使並沒有什麼效果。
當時坐在我身邊的是一對帶小孩兒的父母,那小孩兒被他的母親抱在懷裡,一直吵嚷著要買東西吃,我便分享了自己的橘子給他。
那小孩兒的吃相很一般,汁水濺得到處都是,還沾到了我的白T恤。他母親才剛道完謝又來道歉,忙碌得很。
窗外的風景漸漸變得熟悉,火車駛入辛豐縣境內。我在這裡呆了很多年,自然很熟悉。也就是這個時候,一個女人忽然站了起來。
「完了!我的東西不見了!」
她的聲音尖銳鋒利,在吵嚷的車廂里宛如有穿透力一般。
所有人都看向她。
女人又是恐慌又是憤怒,叉腰喊叫乘務員,然後指著我們所有人說:「今天我的東西不找到,你們一個都別想走!」
我問心無愧,沒什麼好害怕的。
忽然,我聽到火車上有人喊我的名字。
「晏如?」
我下意識抬頭看去,在我座位的斜前方,坐著一個青年男人。他年齡和我差不多,衣著普通,風塵僕僕,看起來和我一樣是個為生計奔波勞累的人。
我覺得他很眼熟,但卻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
在這個時候,被人叫出名字,我心裡沒有歡喜,只有不安。
那個男人忽然興奮起來,無神的眼睛像是忽然被一把火給點亮了。後來很久之後,我反覆思索他究竟想到了什麼,才會露出那樣的眼神,最後也找不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或許是他的生活有諸多不如意,所以在遇見了曾經被所有人欺凌的對象時,又回味起了那種高高在上的,把別人踩在腳下的感覺。
男人站起來,指著我高聲說:「我認識他,他有盜竊史!他高中就愛偷東西!」
那一刻,我渾身所有的血像是被瞬間抽乾,然後整個人被丟進一個冰窟窿。
這種感覺就像是被人扒光了全部的衣服,赤裸裸地丟在人群里。但沒有一個人憐憫,他們反倒都發出嘲弄的笑聲。
又冷又窒息。
那些我以為已經遠去的東西又驟然降臨在我身邊,它們叫囂著,要撕碎我所有的希望,要把我拖回到無底的深淵裡去。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囁嚅著解釋:「我……我不是……」
可男人早就捏住了我的痛腳,那個只需要輕輕一戳,我就會被一擊斃命的痛腳。
我用近乎祈求的眼神看他,可他依然大義凜然地說:「他爸爸還是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大家要注意啊!說不定就是他偷了東西!」
他話音落下,我身邊的夫妻像是沾染到了什麼髒東西一樣,驟然跳開。小孩兒的母親一把打掉小孩兒手裡還沒有被吃完的橘子,她心裡已經篤定我是個不安好心的壞人,覆蓋著友善的面具居心不良地接近他們。
可剛剛她還對我道謝。
我明明什麼都沒有做,也什麼都沒有錯,我和剛才的我沒有任何區別,為什麼事情又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對我有這麼大的惡意呢?
「別怪老同學不給你留面子,我也只是給大家提個醒。我不能因為和你是老相識,就包庇你對不對?」男人說著,眼神移到了我放在車座下的編織袋,「這是你的東西啊?」
我還沒有回答,小孩兒的父親就搶先說:「對!我看著他拎著這個編織袋上來的。」
「打開給我們看看吧,才能自證清白。」
所有人的視線都投注到了我們身上,他們漠然得像是一座座冰雕。
我相信這些冰雕里有很多是等著看我笑話的,因為我的餘光瞥到很多人在偷拍。
如果我真的是小偷,我敢保證那些視頻會滿世界亂飛。甚至即使我不是小偷,視頻也會滿世界亂飛。
沒有人願意多花時間去了解一個殺人犯的兒子是不是真的偷東西了,因為我,本身就是不值得的。
他們願意相信視頻的引導,願意一起感慨「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甚至更期盼東西就是我偷的,那這樣的話談資會更勁爆。
我忽然很恨,但又不知道該去恨誰。我向上帝發誓,向如來佛祖保證,我真的沒有做過壞事,不應該有這樣的報應。
身體開始止不住地顫抖,我努力挺直脊背,讓自己看起來沒有那麼懦弱:「我沒有偷東西,你憑什麼要開我的包?」
第2o章清白
微曜科技大樓的會議室里,燈火通明。
一張十米長的橢圓形方桌占據了會議室的絕大部分,也能夠容納下最多三十人在此處開會。
孟懿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一天能夠坐在這裡面。他身邊是6安弛和秦月章,對面則是西裝革履的許黯然,幾人都把目光傾注到了會議室前方在展示的科技員身上。
在房間的北面牆上掛著巨屏電腦,一個穿著白色大褂的男人正配合著電腦上的內容做著講解。
「我們研發的暴雪,雖然主打解決患者精神類疾病,但我們只是配合腦科醫生的輔助性產品。暴雪會營造一個仿真的具象潛意識層——雪境,也就是俗稱的『夢境』。患者現實中曾經所受的精神創傷會在這裡重現,我們的技術員會根據不同情況為患者制定解決方案,撫平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