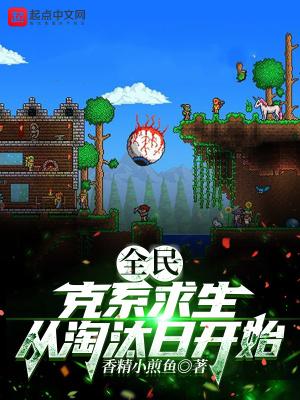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错位剧情 > 第37章 阴影将近(第1页)
第37章 阴影将近(第1页)
之所以庭芳没有选择直接去省城,是因为她对于省城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不可能带小吃车去省城,而且她也听说省城那边对摆摊管得很严,她初来乍到,是不是能找到地方,能不能卖得出去,都不好说。
关键是庭芳去是为了找人,她必须有空闲时间,所以难以去全职打工。她必须找一份工作,既能养活自己,支撑她在省城长期生活,又能方便接近那三个人。
为此庭芳去了人才市场,找了中介,想看看没有学历的中年妇女能找什么工作,中介给她的选择是做卫生,护工,育婴,家政……总之都是照顾人的。
庭芳从来没干过,中介建议她去考个育婴师证,现在正时兴,还能学点东西。于是从来没正式上过学的庭芳开始摸索着报名,上课,考试,学习婴儿的保健护理,了解婴儿生长周期里的各种变化以及心理,学习法律和一些操作技能。
她居然在其中获得了快乐,每天都认真看书,遇见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她反思自己作为母亲的不足,也反思自己人生的纰漏。
如果真能重活一回,庭芳一定选择不同的路。只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庭芳反而更明确了一点,只要把孩子生出来,就要负责到底,哪怕是孩子已经死了,也得让她死得瞑目。
庭芳顺利完成了理论和实操的结业,中介给她派了一家,孩子已经一岁多了,父母工作都忙,有时候夜里才回家,虽然有老人帮带,但家长还是不放心。这个活儿比照顾新生儿容易一些,不过工资却还是高得令庭芳愣了愣。
也可以理解,这个年代,在小县城里还肯找人帮忙带孩子的,肯定是家底殷实。庭芳听中介说省城这种活儿更多,好找得很。
只是工作并没有庭芳想象那么容易,她很努力地做事,孩子的奶奶却仍然看她不顺眼,做了一个月还是结钱劝退了。庭芳有点受打击,其他同样做这行的人却安慰她这是再寻常不过了,工作都是双向选择。
庭芳意识到自己其实根本没有打过工,她现在就和初进入社会没有两样,她强压下急躁,和自己说要慢慢来。那个凶手还很年轻,他很可能再犯案,她还不算老,她还有时间。
第二个雇主对她还是满意的,她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幼儿园,休息日就陪孩子玩,雇主没挑过什么错,孩子也很乖巧。后来雇主问她能不能做饭,可以给她加钱,于是庭芳答应下来,每天多做一份晚饭,孩子单做。
庭芳在那家做了很久,中间她也跟着在人才市场认识的朋友去做过一过性的打扫卫生的活儿,积攒了非常多的经验。只是日子久了,她难免对那家人,尤其是孩子,产生感情,这种感情让她害怕,她怕有一天无论是她要走,还是雇主让她走,都会难以适应。所以差不多一整年的时候,庭芳决定要提离职。
她还没找到机会开口,突然从人才市场的熟人那里听到聊闲话,说一个亲戚的孩子自杀了。
听到“自杀”
这个词,庭芳猛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在正常的生活里过了太长时间,即便是没有忘,却还是有一种突然被拉回现实的恶寒。
她故作无意地搭话:“多大的孩子啊?”
“十七八吧。高中毕业。”
家政阿姨说,“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脆弱啊,总是要死要活的。”
另一个人说:“也不能这么说吧,现在人的压力比以前大啊。”
“小孩有什么压力啊!压力还不是在赚钱的父母身上!”
“他家是二婚家庭,死的那个孩子是男方带的孩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个小的,大的估计是觉得受冷落了。”
他们聊得欢,庭芳好不容易才能插进话:“那孩子是怎么死的啊?”
“听说是开煤气,放假自己在家里,父母出去旅游了。”
庭芳背对着其他人,紧紧闭了闭眼睛,想起当年看见周在尸体的样子,那么安静,就像是睡着了。所有人都说她是自愿的,她就真的是自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