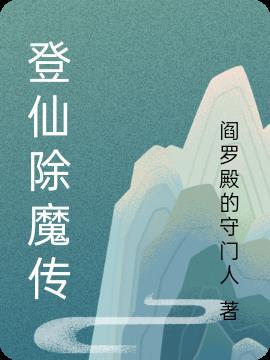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给玄德当主公txt > 第三十七章 一转眼盖世奇功来了今日更8600字求追读(第2页)
第三十七章 一转眼盖世奇功来了今日更8600字求追读(第2页)
那随侍冷的一边往嘴中吐热气,一边道:“家公连续三日去了市中的旗楼,在那里等着汉军前线的消息。”
“那方,能有什么消息?”
胡氏冷冷道。
“夫人不知,驿舍的驿使每个月都会从前线将这一个月的战况带回,咱涿郡的豪绅之,每个月中的这三两日,都会聚集在亭楼等候塞外的消息。”
“诸家豪绅都等在那干嘛?他们的儿子也出塞打仗去了?”
“那倒不是,夫人不知,这前线的胜败与否,关系到幽州下一年乃至于下下一年的歉粮,口算,粮价,马价亦或是各级官员的调离任用,都是和诸豪绅息息相关之事,因此他们格外的重视……”
“行了行了,这些事都让家公去打听吧,我一介妇人不掺和那么多……我只在这等我儿子……”
说到这,胡氏嘴巴一泯,委屈的掉下眼泪来。
那随从见状,很是无奈长叹口气。
看来,一时半刻是回不去家了,只能在这继续冻着。
…………
与此同时,涿县市集中的旗楼上,此刻已经齐至了二十余个本豪右,他们皆是涿县大户,不论是财力,徒户,土在本郡都是屈一指。
而躲在角落的刘周跟这些人一比,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他只是默默蹲在角落静听。
对他而言,别的都不重要,他只需要知道前线的战事情况,知晓自家那两个竖子的生死就好。
与刘周相比,其余那些豪右族主显然是心情不错,众人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的谈说,尽论这幽州各郡当下最为重大之事宜。
刘周并不参与,他也没有资格参与,说白了以他的身份都没资格坐在这里,只不过是走了一下相熟豪右家的后门,硬跟着别人家的家公来这里凑热闹的。
“王世叔,那苏双的事情你怎么也得管管了!”
一名身材宽大的豪右家主,对着一名长者道:“那驵侩联合了中山的张世平,沮阳的冯兰,狐奴的田悟,巨鹿的平惜,乘着马价低时,将河北的马种和私人马场全都收了去,如今这几个人形成了一股势力,垄断了幽、并、冀等大部分的马市,旁人想插一脚都难,如此下去,怕是不出几年,这河北的良马渠道怕是都要被他们给吞了!”
旁边,另一位豪右家主道:“不错!那苏双算什么?区区一介驵侩而已,也敢妄想吃下整个幽并马市?世叔,你确实得找他谈谈了!”
在场众人皆纷纷点头。
那姓王的老者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煽风点火而变的愤怒,相反,他此刻竟是出奇的平静。
少时,却见王姓老者缓缓站起身来,来回扫视着在场诸人,颤巍巍道:“既然诸位都觉得苏双等人当初低价收马种和马场有垄断幽州马市之嫌,那你们当初为何还都抢着卖给他?”
一句话说出来,在场的豪右家公皆不吭声了。
老者见众人不说话,继续道:“只怕是你们当初都得了风声,言朝廷北伐出塞驽马短缺,太仓和方又无多余财帛收马,只能按户强征,你们害怕损失,着急处理手中多余的驽马,让苏双联合张世平等人捡了个大便宜,是也不是?”
“是、是又如何,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又是什么不对?”
一名豪右家公不服气喊道。
“既是人之常情,那人家苏双敢赌这一局,输了,他倾家荡产,赢了,他便可跻身幽州一等豪富之门,位列我等之上,人家输的时候你们不管,如今人家赢了,你们却让老夫约谈他……呵呵,老夫可张不开这个嘴啊。”
那名身材宽大的豪右家主道:“王世叔,您这话就不对了,咱们这些人好歹也是同气连枝,大家数代皆居于此,彼此泾渭分明,少有越界,那苏双不过一驵侩,凭什么坏了涿郡的规律?若不闻不问,今后这界上,怕是什么牛犬马驴的,都敢到咱们脸上踩一脚了!”
旁边还有人煽风点火:“是啊,世叔,您是这里辈分最长的,这幽州的马市生意,难道您家就没有份了么?”
姓王的老者冷笑一声,用手颤巍巍指了指他们。
“你们啊,就会出了事在这呱噪,当初想了个甚来?那苏双虽是驵侩出身,但时机抓的好,此番他收马之后,转头便卖于朝廷军用,不但是以收购价的八成卖,还先货后钱,你们可知,子下定心意北上出征,偏偏后方驽马驮运这块出了问题,”
“苏双却早有筹谋,宁可自家亏本,也帮子堵上了幽州短缺的一半窟窿,如今此人的名字,已经是传送到陛下的耳中了,你们以为,现在就老夫就能动了他吗?”
众人闻言齐齐不吱声了。
少时,突见那胖大豪右不服气道:“王世叔,糊弄我们不是?雒阳的事情您老如何知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