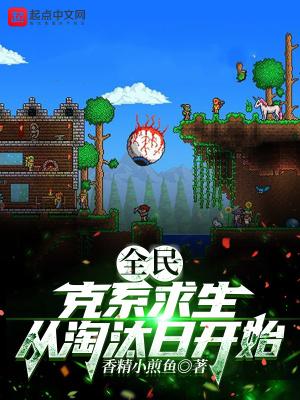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偏心是什么意思 > 第75頁(第1页)
第75頁(第1页)
醫生不能站在本職角度給出無效的建議,他只好說:
「董事長,趙炎這邊您看。。。。。需不需要給予一定劑量的促紅素治療。」
趙老太太瞪了他一眼,顯然不是第一次接受這樣的建議,卻沒有一次能讓她如此生氣。
「那個野種是要死了嗎?」
「那倒沒有。」醫生回答謹慎了許多,「趙炎只是嚴重的過敏性貧血,在基因不存在缺陷的情況下,自身的紅細胞再生功能是可以慢慢修復的。」
「基因不存在缺陷!」老太太的聲音陡然尖銳:「我投給你們國內國外多少醫療設備和實驗室,現在給我來一句基因不存在缺陷,憑什麼我的兒子孫子基因缺陷問題遲遲得不到改善,還要被迫承擔遺傳的風險,那個野種卻能擁有健全的基因!」
趙老太太躺在沙發上,閉上雙眼流出眼淚,她握緊胸口的那枚寶石胸針,名利浮華於她而言仿佛是惡毒的詛咒。
「翊君不是要治療嗎,就抽趙炎的血吧,這是他欠我們趙家的。」
她像一個世無可戀的幽靈,殘忍地要將一切同歸於盡。
醫生立刻阻止:「董事長,醫院的血漿充足,真的。。。。。沒必要這樣的。。。。。」
老太太不說話,眼睛也懶得睜開。
「董事長,美國擁有目前最先進的基因編輯技術,如果我們把趙炎和趙總的血液樣本送去分析,實現殘損基因修復,對於阻斷遺傳是非常有效的。」
「哦?」趙老太太問:「為什麼之前沒聽你們提起呢?」
醫生只好解釋:「實驗結果需要大量比對,考慮到趙炎的身體狀況,不適合進行採血。」
趙老太太冷哼一聲,沒再說什麼。
在趙老太太和醫生談話的這段時間裡,趙炎一直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護士給他準備了早餐,叮囑他抽完血再吃。
麵包看起來很鬆軟,趙炎用手捏了捏,護士笑他可愛,又多送了他兩顆奶糖。
趙炎說無聲的謝謝,撩起袖子讓護士給他扎針。
青紫的血管輕易被找到,塗上碘伏,刺入針管,趙炎偏過頭不敢看,他覺得又疼又冷,血液流失的感覺如同燃燒一盞油燈,慢慢地油盡燈枯,人死就如燈滅。
趙炎趴在椅子的扶手上,白色毛衣遮住口鼻,他的眼睛盯著走廊盡頭的那扇窗戶,光亮中一片虛晃的白,他開始目光放空,眼皮很沉,感覺時間越來越漫長。
趙炎終於忍不住好奇,回頭看了一眼,霎那間,流經心臟的血似乎凝成了冰,凍的整個胸腔又冷又疼,趙炎變得呼吸急促,眼淚流個不停,整個人僵著動不了。
他弄不明白那隻透明儲血袋的意義,只知道血液從他身體裡抽走,便成了不屬於他的東西。
這種類似搶奪的行為,幾乎每次體檢都會發生,卻是第一次,趙炎發出怪叫聲一遍遍喝止護士,又因為被無視,只能憤怒地拍翻了放在盤子裡的兩顆糖。
趙炎不停搖頭,在感到一陣頭暈目眩後,迅逃離了椅子,終止了不斷流經塑料管的血液。
血順著他的手臂蜿蜒曲折地淌了下來,點點滴滴落在了白毛衣上,看上去很悽慘。
護士尖叫著,醫生衝進來,四五個人把趙炎毫無尊嚴地按在床上,他張著嘴卻發不出叫喊聲,只能仰望頭頂的白熾燈流淚。
「準備好重紮針。」
趙炎的兩隻手都被綁上了止血帶,他掙扎得厲害,手臂上的血管也越發清晰。
「怎麼辦,他太痛苦了。」護士變得不忍,她按住趙炎細瘦的手腕,失血后蒼白脆弱的手,顫巍巍又無力蜷曲,手指變得有些僵硬和發青。
趙炎應激到整個人發抖,在醫生放開他後,他近乎脫力地滾下床,縮在牆角抱緊自己的手臂和膝蓋,蜷縮成一團。
「不能繼續了。」醫生似乎為此而羞愧。
「誰說的。」趙老太太脫了外套,坐在一張輪椅上,歲月好像帶走了鮮的血肉,只留下一副僅存執念的枯骨。
她停在趙炎面前,敲著拐杖問他:「趙炎,你哥哥對你那麼好,你難道不願意救他的命嗎?」
趙炎害怕地退後,背貼著牆壁,直至退無可退。
「趙炎,你的命是翊君救的,人要懂得知恩圖報。」
趙炎抬起頭,因為有話要說,只好請求奶奶把手機給他。
他的袖子還挽著,兩節手臂白的晃眼,伸向趙老太太的一瞬,被拐杖狠狠打了回去。
「別碰我。」
趙炎呼不出痛,他疼得縮回手,眼睛紅紅的,皮膚被拐杖打出悶重的聲音,留下一道深紅的血痕。
他點頭,像只蝸牛慢慢縮回身體建築的外殼,抱緊膝蓋的樣子渺小又可憐。
「你和姓林的那點事,我已經知道了。」
老太太抬手示意,手下便拿出手機里的照片遞給趙炎。
「他和肖玉還真是般配呢。」
趙炎恍惚間聽到熟悉的名字,他仰高頭,臉色慘白,林業斐和肖玉的合照毫無預兆地放大在眼前。
一個西裝革履,一個巧笑倩兮,肖玉彈著鋼琴,林業斐戴那副熟悉的金絲眼鏡,微眯著眼望她。
另外一張照片,肖玉做了個邀請的手勢,林業斐身姿挺拔地邁步,走向了她。
趙炎怔忡間以為聽到了玻璃碎裂的聲音。他抬頭望了望窗戶,外面電閃雷鳴,風吹折的樹枝要掉不掉地懸著,看起來搖搖欲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