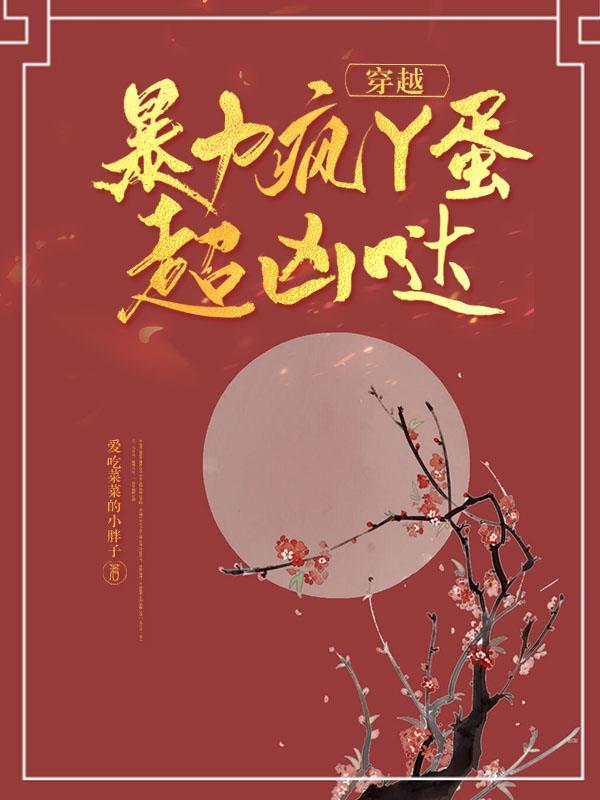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超级渗透剂ftrt > 第20章 大兴安岭的第二夜故事纸片小人上(第3页)
第20章 大兴安岭的第二夜故事纸片小人上(第3页)
“原来是个疯子。唉。”
齐广生回到家中已经是中午,肚子饿的咕咕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嚷嚷道:“妈!妈!做饭了吗?”
等了老一会也没有动静。齐广生满心恼火走进卧房里去,却见卧房无人,再去厨房也是空空如也,揭开米缸只见薄薄的一层米睡在底部,齐广生一边喃喃地骂一边抓起火石生火,可是平日里没做过炊,老半天也点不着柴,一气之下东西一摔不吃了。
睡个午觉起来肚子反倒不怎么饿,他又想去赌场观看,却被伙计刁难没本钱不让进场。晚上回到家,母亲还是没回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齐广生这才知道自己是真的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落到在家等死的份,不禁潸然泪下。
“算起来过几日便是初十四,要不……就去瞅瞅吧。假若那老丐说的是疯话,死在哪里埋在哪里便了。”
他悲从中来,生出破罐破摔的心思。打定主意就做准备,将家中仅有的绳索镰刀米酒能用的物什打包带上,缸底的碎米熬了一碗稀粥喝。次日就从奉天府出,往东南边去。
时值初夏,道路干爽好走,齐广生饿了就采些野果野菌充饥,一路还算顺当。两日后到达张家堡,折而向东,原本车马驰道变成了乡土小路,两侧是布满荆棘的树林。齐广生担心走到野外不好露宿,加快了脚步,但终究是战战兢兢的在野外将就了一夜。
第四日早间齐广生正饿得慌,忽然见到前面有一片梨树,结了大小不均的梨子,当即赶过去,将包袱放在地下就爬上树去边摘边吃,吃了几枚也就饱。要下来时,却现有两个人正在翻自己的包袱。他忙喊:“干哈呢?”
那两人翻看包袱没啥值钱的,一人对另一人说:“切,是个水码子。”
另一人指着齐广生说道:“你给我下来。”
齐广生跳下树来,只见这二人都是三粗五大、面目凶恶的汉子,一个壮一个秃,先自怯了。一人揽住他肩没好心地问:“兄弟有钱吗?借点来使使。”
齐广生知道遭了贼,主动把身上的兜都翻过来,卖惨说:“我现在是贫困潦倒,正要去阴魂镇投奔亲戚。”
两个贼闻言相视一眼,随即哈哈大笑:“你你说什么?去阴魂镇投亲戚?哈哈哈哈哈,得劲。”
笑罢,秃子突然想到什么,转了个语气问:“哥们莫不是里码人?报个蔓儿?”
壮匪却不屑的道:“得了吧,你见过绺子这么白白净净的?”
“也是。”
秃子回答,拨开衣衫亮出腰间的盒子炮又对齐广生说:“这一带哥俩熟得很,你可别瞎几把扯淡,小心吃飞子。老老实实说干嘛去。”
齐广生吓得打抖,于是把自己败光家产走投无路,听信乞丐的话去寻找山中柜坊的事简略地说了。两个贼人听完笑得更是不可仰,不过反而客气了些。
秃子说:“哥们,你都穷成这样了,兄弟也不来为难你。可那阴魂镇只是一个地名,并不是一个镇子,你听名字就该知道那地方邪乎的很,一到夜里就鬼哭狼嚎的。我俩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还不敢往那边去,你要是真的敢去,我俩反倒有几分佩服。”
壮匪竟然掏出一块饼递给他,说:“送你了,你要是有命回来,倒与我说说那山中的柜坊究竟是啥样。哈哈哈哈哈!”
齐广生作别贼人,心下更加恐慌,其实已经萌生退意,但想自己不学无术就算回去也迟早是饿死,只好硬着头皮向东行又行了一日。
这天傍晚来到一处简陋的界碑,赫然写着阴魂镇三个血红大字,算起来正巧是初十四。这地方果然不是镇子,按规模说最多也只能叫屯,只有寥寥四五间残垣断壁,到处生满茅草,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人居住过。这样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活人的痕迹,只怕自己是上当受骗了。但赌徒的心态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对自己有利,也选择欺骗自己,更何况是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