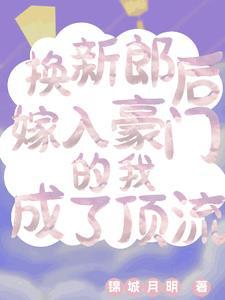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权臣的在逃白月光全文 > 第八十章 她待他又有什么是真的(第2页)
第八十章 她待他又有什么是真的(第2页)
此番他来回禀,更不会提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需要顾飞提醒的“谨慎些”
。
裴宥已升官至侍郎,在工部有独立的办公隔间,加之此刻深夜,整个工部唯有他一人而已,徒白同在清辉堂的书房里一般,直接回禀。
当其冲的自然是江南一案带来的朝中动荡,两江总督的动向。
接下来回禀了李谙的动向,这些日子查来的宜春苑的消息。
甚至裴宥离京之后,工部的一些动态,也捡着看来有必要的,禀了几句。
裴宥的桌案上堆满了公文,他似乎不觉疲累,烛光下侧脸清俊,薄唇轻抿,徒白禀一句,他“嗯”
一声,遇到疑惑多问几句,与往常无异。
禀报结束,徒白照例等着裴宥的下一步指令,那厢却迟迟没有动静。
徒白抬头,便见他阒黑的眸子正望着自己。
他心下一凛,忙垂下眼:“公子可还有何吩咐?”
裴宥像是笑了:“我离京前给你的任务为何?”
徒白莫名觉得他是被自己……气笑了?
难得的背上沁出一股汗意,忙道:“公子,温家酒坊一事,徒白已查出,既不是温家大公子出资,亦不是温家二公子出资,而是温家那位姑娘出资。只是她的银子来源,因时日已久,目前只查到她当过许多饰,且或许与一家地下赌坊有关,但还未及明确,因此未向公子禀明。还请公子再给徒白几日时间,徒白必将来龙去脉查得一清二楚!”
“还有呢?”
徒白眨眨眼,还有……
他突然想到顾飞刚刚那无声的三个字,瞬间心下透亮。
“回禀公子,温姑娘择婿以来,考虑过三位公子,一位是大理寺丞家的曾公子,也正是屯田司的郎中曾绪,一位是吏部秦尚书的侄儿秦羽,还有一位是京中富商燕礼,亦是云听楼等几家酒楼的老板。其中见过曾公子与燕公子,曾公子是温大人相邀,于府上相见,并无下文;而燕公子,相约于府外,云听楼见过一次,又于今日相约于天山池。”
徒白禀事,向来简明扼要,不报过程,只报结果,还是头一遭将事情说得这么详细。
只觉书案前的裴宥情绪越来越淡,淡到他察觉不出自己所禀的内容到底是不是他想听的。
但话已至此,他也就硬着头皮将最后一句话说完:“今夜温家一番商议,五日后,燕礼上门提亲。”
顾飞连番好些日子没有好好歇息,实在累极,听着里头一时停,一时起的声音,具体说些什么当然是听不仔细的,但便是如此,才更让人犯困。
最后竟真的迷迷糊糊打起了屯儿。
一直听到嘎吱的门响,见到徒白黑着一张脸出来,一个激灵站起来。
也不等他问两句话,徒白就一个窜身先走了。
再侧耳听屋子里。
静。
死一般地静。
良久,久到顾飞几乎又要靠着门睡着,里头突然传来一声叫唤:“顾飞,上冰鉴。”
冰鉴?
他蹭蹭被夜风吹得有些凉的手臂,这才五月,上冰鉴?
更何况,这是在工部,不是国公府,哪儿来冰鉴?
裴宥似乎也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开了门,抬步就走。
这是今日的第二次,滴水不漏,运筹帷幄的裴大人,给了仿似完全不经大脑的指令。
-
一连几日,顾飞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水深火热”
。
当然,王勤生也一样。
他伺候了十几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