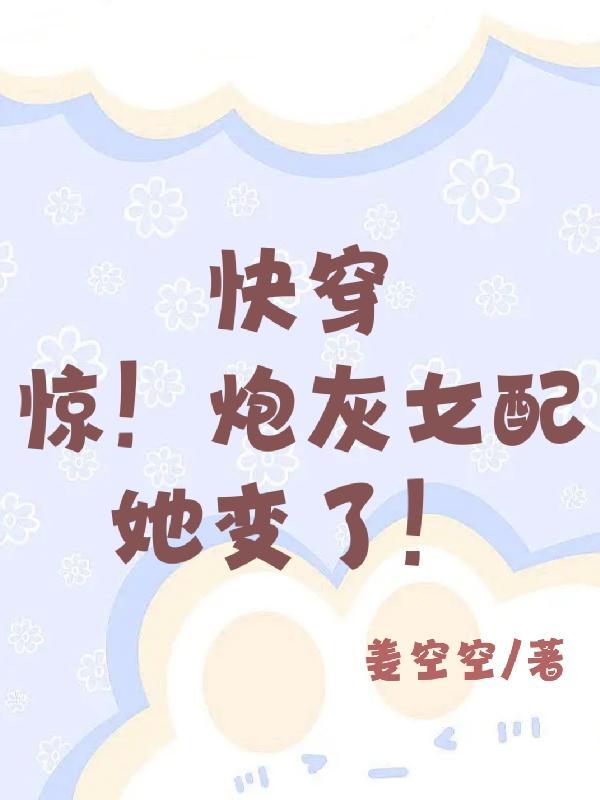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将军的娇宠小娘子 > 第76章 明月照我心(第2页)
第76章 明月照我心(第2页)
聂屏书感觉到周围的那些兵士们盯着明月的时候,都是肆无忌惮的。
她立刻明白了几分,却是不解:“你不是绿绣楼的花魁娘子吗?又不是军中营帐的军o妓,为何要做这些事?”
明月越期期艾艾:“他们兄弟给了妈妈六千两,妈妈自然乐得将我送来。”
刘家的家底如此丰厚,六千两都拿得出来?
聂屏书正嘀咕着,就听到沈江屿那仿佛淬了冰一样的声音响起:“放开。”
聂屏书本能地松了松手,才意识到是沈江屿在拉着自己的手!而他的目光,则是看着明月姑娘拉着他的那只手。
明月姑娘的眼眶瞧着就越红了起来:“沈将军当真对奴家这么狠心?”
可沈江屿的眸色越来越难看,吓得明月也不得不放开了沈江屿的手。
沈江屿只是拉着聂屏书一直往外走,聂屏书回头看明月凄惨站在那里的样子,都忍不住吐槽沈江屿:“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
沈江屿冷哼:“她话太多了。”
聂屏书打了个冷战:“那我以后也少说些话好了!”
沈江屿白了聂屏书一眼,聂屏书委屈:他怎么又生气了?
——
沈江屿对战刘星海一招制敌的事情,很快就在林阳县传开了。
聂屏书这云顾花坊整日门口也来了许多人,都想瞧瞧如此厉害的沈江屿,实在是恼人得很。
这两日聂屏书没少见到二婶婶和三婶婶往对面的铺子里头跑,想来是要和对面商议买铺子的事情。
聂屏书也总是在花房里大声说话:“你们瞧瞧,咱们这门口整日里都要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了!这样下去,还怎么做生意啊?不如扩大了店面,看看能不能将周围或者对面的铺子也扩进来的好!”
每每她这么说话的时候,吕四娘就凑了过来竖起耳朵听着。
聂屏书继续叹息:“就是如今这铺子实在是紧张。咱们崖州这两年风和日丽,是好年景。来林阳县做生意的人也多,只怕若再晚,铺子就该没有了!不成,我得尽快去把钱庄里的钱取出来,然后四处问问铺子的事!”
她话说完没多久,吕四娘便没了人影。
阿幸也不满地走向聂屏书:“屏书姐,这吕四娘也太过分了吧?我亲眼瞧着她从后院溜出去了,只怕是去找二房他们通风报信了!”
聂屏书胸有成竹:“我就怕她不通风报信!你这两日带着她,感觉怎么样?”
说起这个,阿幸就来气:“可别提了!知道的是晓得她来花坊做工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做大小姐来的呢!你在的时候还好些,她多少顾及些你,装模作样也知道干点儿活。可你不在的时候,她是动都懒得动一下!时不时地还想指挥我,若不是我脾气大,只怕早就被她当小厮丫鬟使唤了!”
她又指了指后院做小工的几个丫头:“那几个就可怜了。她平日总在花坊说她是你们的表妹,那几个都不敢招惹她。什么端茶倒水,送花摘花的,她尽是叫那些丫头去做了。她还说想学花艺,我看她是想空手套白狼!”
聂屏书的嘴角勾了勾。
她还没动脑筋呢,“敌人”
就开始自败了,这不是正合适?
她对阿幸道:“花艺自然是要教给她的,不过不必太用心。而且我要你时时刻刻夸赞她的花艺做得好,看她是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