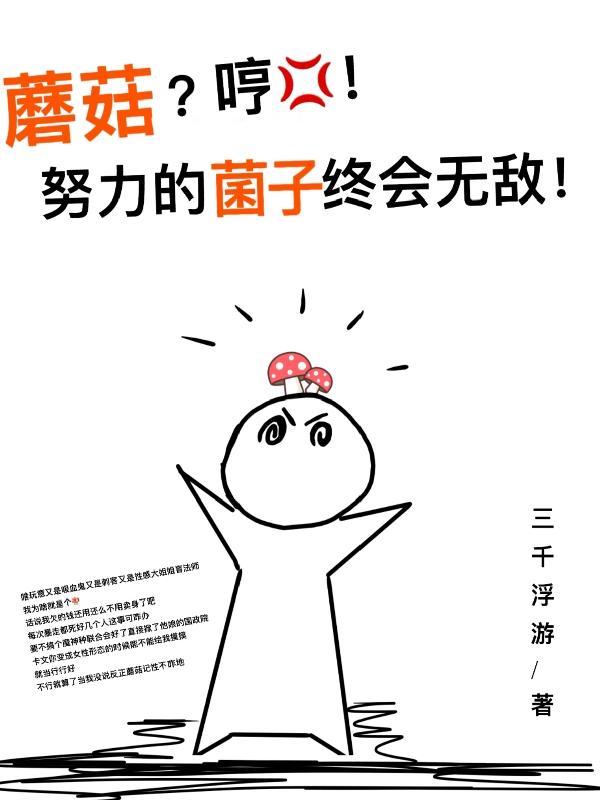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古典制约作者蒸汽桃免费阅读 > 第 20 章二合一(第2页)
第 20 章二合一(第2页)
每周末燕知要开车去市里的海洋馆打工。
路上是他最轻松的时间。
他控制不了什么时候不让牧长觉来或者让牧长觉消失,但是每次他想要牧长觉出现的时候,他总是会来。
就像是过去牧长觉承诺过的。
“只要你开口。”
明知道是不对的,燕知却总忍不住在开长途的时候找牧长觉说话。
他喜欢跟他讲最近自己做了什么实验,学习了什么理论。
他给牧长觉讲自己那个关于成瘾的课题有着怎样令人骄傲的进步。
“牧长觉,我是你的骄傲,对吗?”
“只要我能控制,我就不用离开你,对吗?”
有人追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他读诗。
燕知笑着问空气:“你会吃醋吗?”
乐此不疲。
换药后的第一个周末,燕知刚开上高速就想跟牧长觉说最近自己没头疼了。
但是可能对这个话题没那么感兴趣,牧长觉没有如期出现。
燕知频繁地看自己空荡荡的副驾驶,换了一个话题,“我返回去审稿的文章已经接收了,下个月初就能在顶刊线上发表。我还拿到了今年的第一笔独立经费。”
他当然是牧长觉的骄傲。
牧长觉对他的任何一点成就和进步都是绝对自豪的。
过去燕知上学拿的各种奖状奖牌家里都放不下了,牧长觉连他得的“重在参与”
塑料小红花都舍不得扔。
发表学术论文和拿到独立经费是他科研工作中的重大进展,牧长觉不可能不关心。
但是那辆四手破尼桑里,只有燕知一个人自言自语。
他心跳变得快起来,控制不住地往下压油门,“牧长觉?”
燕知意识到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虽然他总说自己可以控制。
当初车的前主人交车时,跟燕知开着玩笑说:“这辆车已经快和你一样大了,答应我不要开过一百英里每小时好吗?”
一英里是一点六公里。
当那辆尼桑以将近二百迈的速度扎进绿化带的时候,燕知还在想:牧长觉为什么不来?
那一次他非常幸运。
幸运到他可以清醒地从一个急救室独自步行到另一个急救室。
其实燕知除了一些皮外伤,只被气囊撞裂了两根肋骨。
光片上很细小的裂纹,凭借肉眼的视力几乎无法发现。
只是按照这里的医疗流程,像他这种严重的交通事故,要进行及时详细
的全面身体检查。
从医院出来(),燕知有条不紊地和保险公司对接完成了车辆报废(),又坐城际列车到车管局做了笔录,确认自己不适合驾驶,签署了同意永久性吊销驾照的调查决议。
他习惯了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燕知想通了问题的症结。
“我对新药过敏。”
燕知对林医生说道。
那天离开诊疗室的时候,燕知手腕上多了一根黑皮筋。
他走到哪儿都戴着。
像是一道可以保佑他的护身符的护身符。
从那个时候开始,燕知更努力地集中在他的课题上。
与其说他在研究怎么戒掉,不如说他在研究怎么不戒掉。
他躺在出租屋窄小的单人床上,搂着一张不存在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