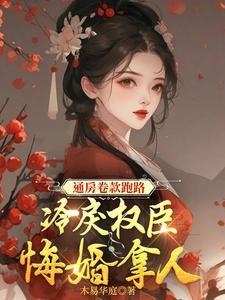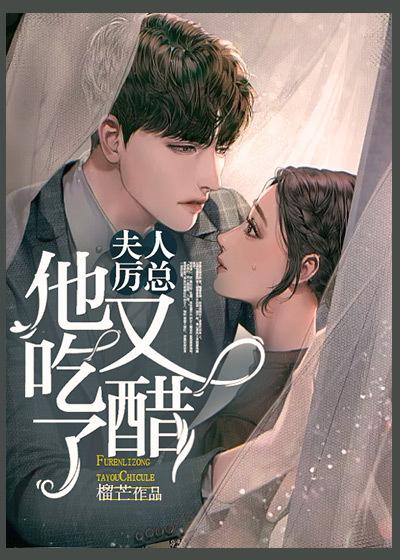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知我者谓我何愁不知我者谓我何忧 > 第一章 芝兰玉树(第2页)
第一章 芝兰玉树(第2页)
一阵风起,窗外飘进几片竹叶,落在李元辰未完的《瘦竹图》上,倒似浑然天成。李元辰眼光落在其上,恬淡道:“臣弟不比皇兄有经天纬地之才,但求独善其身。”
“辰弟不必过谦,当年天育寺与帝师苏公望一番考较,可是成就吾朝一代佳话!只不过世人不知当年那个“小沙弥”
即是今日的容亲王世子罢了。”
李元辰十二岁那年,因病寄养于益州天育寺,寺中高僧玄智大师见其才思敏捷、天资出众,便于闲暇时授他梵文典籍。想不到他竟能过目不忘,半年之后,梵文于他便如本朝国文一般无二。
那年冬日,帝师苏公望到寺中拜会老友,与玄智大师抵足长谈,无意中谈及此子。苏公望一代名儒,位及帝师,难免有些自负,质疑小子不过半年便能精通梵文,因此约定次日考较一番。
早课过后,玄智大师领着李元辰来到禅房与苏公望相见,李元辰见长者在上,便恭敬执礼。苏公望阅人无数,当时便觉此子如璞玉浑金,俊雅脱俗,便如伯乐见了千里马般,连连颔首,喜不自胜。
玄智大师居中位,李元辰与苏公望一老一少隔案而坐,用梵文引经据典、以史带论。初时李元辰还顾及长幼尊卑,未敢在长者面前太露锋芒。奈何苏公望爱才心切,一味想逼得他尽展所学。李元辰到底年少气盛,终无顾忌将自己所学发挥地淋漓尽致。两个时辰过后,苏公望终于诚服此子梵文造诣在他之上。
当时,苏公望曾一再追问此子来历,并想将他带回京师,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无奈玄智大师任凭他如何相询也缄口不言,还颇为自责道:“此事原是老纳一时起了执念,老纳也是受人之托,不敢妄自相告此子来历。再来,此子固然天赋极高,只是体弱多病,心思甚重,正所谓慧极必伤,旷世才学于他怕反受其累,岂不闻福祸相依?”
一席话直让苏公望黯淡长叹,只得抱憾而去。也因此,这段佳话流传至今,世人只知天育寺中的“小沙弥”
。
“臣弟惭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相较苏太傅之博学,臣弟所识便如萤火之于日月,太傅当年不过是看臣弟年幼,又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憨态,才与臣弟一戏,岂可当真!”
李元辰笑着轻轻摇头,心中颇感无奈,只怪自己当时少不更事,惹了这闲名。
侍女奉茶上来,李元辰欠身恭请道:“皇兄品尽天下名茶,且试试此茶,可还能入口?”
叡帝轻启碗盖,便觉清香扑鼻,以他对茶的嗜好却叫不出品名来,轻含了一口,只觉其味清苦而后甘凉,回味持久,齿颊生香,“辰弟此茶可有名目?”
李元辰也浅饮了一口,“此茶名为“皋卢”
,产于益州,虽不闻名,却是臣弟从小吃惯了的,母妃每年都会着人送些来。”
“原来如此”
,叡帝抬手又饮了一口。
忽有府中仆从进前呈报,“启禀世子,益州府上有信来。”
“哦?”
李元辰接过信函,函上娟秀的字迹甫一入眼,眉眼间便不自觉地荡漾起了笑意。叡帝不禁纳罕从来云淡风轻的堂弟何曾有过这番神情,“可是皇婶来的书信?”
“回禀皇兄,是舍妹的书信。”
“哦?!可是先帝所封的菁若郡主?”
叡帝一时神思悠远,回想起来还是先帝四十寿诞时遥遥见过一面,彼时自己尚是东宫。听闻皇叔对这位掌珠极为宠爱,是府中上下唯一敢捋“虎须”
之人,想来如今已是娉婷之姿。
“正是”
,匆匆一瞥,李元辰笑意更盛。叡帝不禁更为好奇,一脸探究之意展露无遗。李元辰按下信函,忍着笑意道:“让皇兄见笑了,舍妹顽劣,耐不住母妃管束,想来京中小住。”
叡帝和颜悦色道:“如此甚好,兄妹得见,亦可慰辰弟思乡之情。”
李元辰起身恭敬执礼,“谢皇兄体恤。”
时隔三年,也不知这小丫头又长出多少鬼灵精来。
叡帝闲闲起身,不着痕迹道:“辰弟终日呆在府中,岂不生闷,难得今日秋高气爽,陪朕出去走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