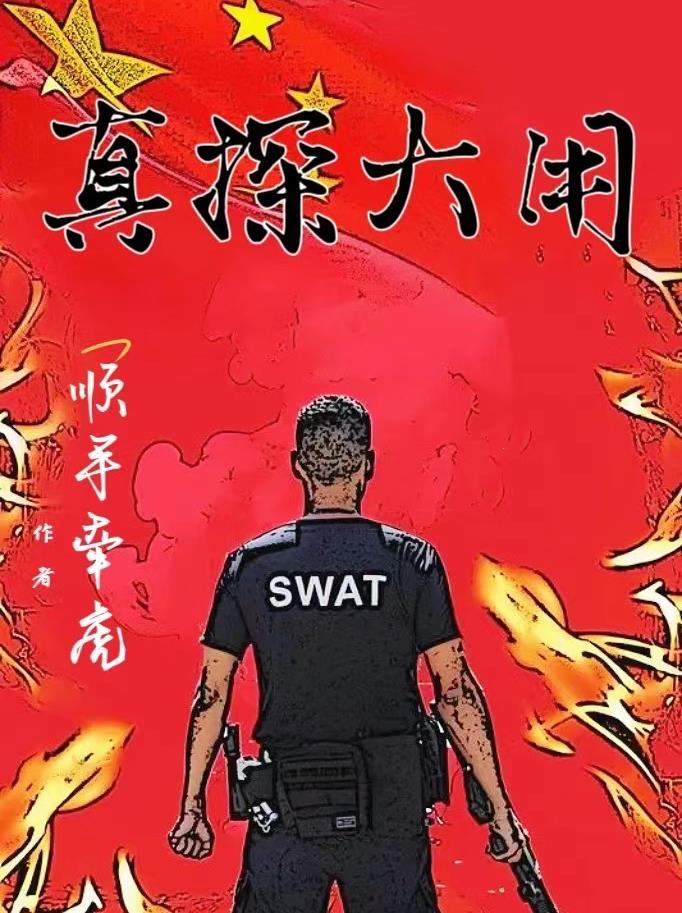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荒村古诗 > 第41章 遇恩师借酒解怀过船闸化险为夷2(第1页)
第41章 遇恩师借酒解怀过船闸化险为夷2(第1页)
闸上的喇叭里喊道:请179号至186号准备过闸。金城道:到我们了,我们是18o号。遂收起扑克牌,大翠男人嘀咕道:我们快要打尽了,这局肯定我们赢。成美男人道:总归有人输赢的,打不尽过了闸再打。船闸门徐徐打开,里面的船依次驶出。金城道:各人上各人的船,把篙子拿好。打帮的解了缆绳,忠礼对老者道:我们先过闸了。老者道:小水的时候注意安全。忠礼等人应道:晓得了。两条船并排进了闸塘。金城、成美男人等人在一条船,他们的船靠在闸塘壁,金城在后尾子拿舵,成美男人在船头带缆,将缆绳吊在船闸的锚钩上。忠礼等人的船只靠在外档,大翠男人撑舵,忠礼将缆绳搭在里船的锚柱子上,手拽着缆绳的头。二墩子则在船头荡着食刀准备剁肉。喇叭里广播道:各船请注意,闸塘开始小水了。忠礼感觉船己下沉,只听金城大喊道:不好了,船歪了。忠认朝里船望去,只见里船朝外歪着,船边离水只有两三寸,金城急得朝成美男人大喊:快松缆绳。成美男人没了章程,瘫坐在船头,其它船上的有人见状,大喊:用刀砍缆绳。话音未落,忠礼迅反应过来,弯腰抄起二墩子手里的食刀,一个箭步,跨到里面船头,对准缆绳,用力猛砍,一声闷响,缆绳断开,船身剧烈向里一歪,又向外晃去,几个来回方才稳当。忠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上了自己的船头。才觉得浑身汗如雨下。成美男人尿了裤子,船头一片潮湿。
过了船闸,行了三五里水路缓弯处靠下了船。大伙儿才平稳下惊魂未定的心,二墩子生火烧炍。金城道:今个儿就不赶水路了,大家吓得不轻,定定心,明个儿早些开船。大伙儿都团着成美男人身旁,成美男人见船靠下来,才慢慢缓过神来,金城对他说道:你小时候用过大船的,怎么把个缆绳打了死扣?成美男人道:我记得是把缆绳搭在锚钩子上的,不晓得怎么多绕了一圈,被鬼木住似的。有人道:做一辈子老娘还把个脐带掐断呢。金城道:今个儿要不是忠礼反应快,就出大滑子了。成美男人道:今个儿事,家去干万不能对我女人说,她要抱怨我死了。今晚的酒肉菜金钱算我的。
一帮男人离了自家女人,没了管束,喝酒嚼蛆,荤话不断,几杯酒下肚,早己把过闸的惊吓撂到溜沟西里去了,尤其是那个李金城,平时撩骚惯了的,只听他先调侃了一阵陈国民。二墩子是老实头,那经他逗呀,把他和学妹做的那个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成美男人道:便宜要你拾去了,落得你说拐话,我家那口子怎样怎样。大翠男人道:我家大翠……金城笑而不语,心里话这个我比你清楚。大伙儿也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只是不敢明说。忠礼一言不,成美男人对他说道:赵小三子,你家小蛮子呢。忠礼道:你们嚼你们的,不要带上她。便不再搭理他们,自顾吃肉喝酒。大伙儿从下傍晚一直吃到星齐月亮出下露水,把个船头弄得一片狼藉,拱到船舱里横七竖八地呼呼大睡。
金城醒来,觉太阳晒进了舱鼓里。赶紧喊醒大伙儿,烧了早饭吃了赶水路。顺流顶风不好扯帆,便着人上岸拉纤。溪河两岸,有现成的纤道。但道这拉纤的苦楚,有人写了现代小诗:枯水的季节,汗水浸透了腰间的纤板,重复前人的脚印,踩出无数个艰辛,唯有——希望在纤绳的那头延伸。
氨水船停靠在生产队庄子后面的大堆边,陈队长安排人连夜将氨水分装几条小木船上,腾下水泥船给下一个生产队去县城。
鸡叫头遍,忠礼忙停当回家睡觉,淑芬小解过后上铺睡不着,想拱在男人怀里亲热一番,忠礼像个死猪似的,沉沉地睡去,淑芬没了兴致。也不忍心叫醒丈夫,闭起眼睛胡思乱想,刚搭着了,小雪又醒了,她把了文美一脬尿,哄着了文美,窗外己泛白。陈队长催煮早饭的哨子在庄子上响起:各家各户起来煮早饭了,吃过早饭男女劳力都去田里浇氨水。
李金城一大早上把船撑到田头,妇女们还没上工,只有大翠子拿着粪舀子站在圩埂上,金城道:大清早上就来上工了?大翠打趣道:等你的,两三天没见了不想你呀。金城笑道:想我也没有用呀,没你家男人硬正,我只能背地里。又问大翠道:王学军回去要没要呀?几天没弄了,肯定急猴急猴的。大翠啐道:一大早上就没得个正言,我问你,你们去装氨水,没事情做,是不是拿家里女人嚼的?金城道:什么意思啊?大翠道:我们家那口子一到家就拱到被窝里,要看我那个。金城笑着说道:他自己嚼的,又没有人掰开他嘴。大翠道:男人没个周正东西,都是骚怂。金城道:又不是我要他们说的。大翠道:还说什尼的?金城道:成美男人说了他女人这块那块的。大翠道:看他平时老实头话不多,也会胡说八道的呢,真是老实驴子偷麦麸子吃,你们男人离了女人有个梯子就能上天。两个人正说着,何小丽扛着舀子过来了,见两人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便道:两个人大清早上说什么情话呢呀。大翠道:嚼舌头根子呢,当心把你x嘴撕烂的。又道:主任女人今个儿怎么下地干活了?什么时候看得上这几分工了?小丽道:瞧你说的,好像我没下田做过生活似的。大翠道:看你穿的俏刮刮的,像个小知青似的。小丽道:队长说是抢着把氨水浇下田,时间长了氨气会跑掉呢。社员们66续续的上工了,大伙儿开始干活不提。
休息的时候,男女社员们坐在农渠边闲谈,士英一阵犯胃,打起了干哕,成美笑道:她大妈怎么了?是伤风了胃口不好还是拣嘴了?士英道:应该是怀住了,身上个把月没来了。大翠道:忠仁大哥放鸭子,整天猴在荡里,哪有空子理摸你的呀?有人接过话茬子:大爹爹有病期间,忠仁不是天天在家的呀。大翠又问一旁的何小丽:主任夫人,你们家大牛假三岁了,肚子怎么老不见动静呢。小丽道:不像别人在人前背后显摆而已。坐对面的淑芬小声说道:小心大嫂听到。小丽四周扫了一下,见士英在不远处,正朝着她望呢,便不再作声。成美说道:几个月了?小丽道:四个多月了。成美道:四个月,看不出肚子来。
忽成美觉得内急,本能地欲解裤腰带,见不远处坐着几个男子汉,便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死远点嘛。吴文喜道:你尿你的,哪个没见过那个呀。成美道:你有胆子不走,看能不能把你裤子扒掉。吴文喜领教过几个妇女的利害,他们是说得出做得出的,遂赶紧爬起来走远了,其它几个男子汉也走到田头。成美褪下裤子,蹲下,露出屁股,大翠子用泥垡头朝她屁股上砸去,成美骂骂咧咧道:哪个小婊子砸的?大翠道:哪个叫你屁股撅多高子的呀。成美道:有什么稀罕的。大翠忽然想起上工前金城说的话,便道:成美,听人家说你那个跟个松蒲包似的,正好给我们看看。成美提起裤子,系好裤带,问大翠道:你这话听哪个说的?大翠自然不敢说是金城告给她的,遂说道:你家男人装氨水跟他们说的。成美男人正在不远处田埂上抽烟,成美气呼呼的过去,掴了男人一个嘴巴子,把个男人打得满眼冒火星子,对成美吼道:你什么神经了?人物溜溜地跑过来就打。成美道:你x嘴作淡了,跟那些骚男人说什么松蒲包不松蒲包的,你嫌松,家里的小白狗紧呢,你去跟它睡去。成美男人晓得有人走漏了风声,自觉理亏,不敢顶嘴,赵成美得理不饶人,指着他鼻子,一通大骂,男男女女都过来看热闹,原指望能有好戏看,不想成美男人怂在那儿,大伙儿有些扫兴。陈队长过来了,训斥道:不好好干活,两口子跑田里吵什尼架,扛什尼嗓。成美气鼓鼓地走了,众人也散了,去上工干活。
大翠男人一切看在眼里,摆在心里,中午回家吃饭,不大搭理自个儿女人,等到晚上脱了衣服上床睡觉,王学军想起白天的事,便对女人大翠说道:你听哪个说成美的。大翠不作声,假装睡觉,学军又道:是不是李金城跟你说的,怪不得一大早上就去田里了。大翠道:你还有完没完了?你们男人在外面瞎嚼女人倒有起理来了,人家李会计告诉我这话有什么?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是不是怀疑我跟他大清早去拱麦棵了?王学军本想借话题作女人一通,不想反被女人抢白了一顿,再加之困了,便不再言语,沉沉地睡去。
赵妈妈烧好中饭,装了一碗饭供在赵老爹七单子下面,嘴里祷告着:老头子,吃饭了。然后全家人坐下来吃饭,士英没吃两口,打起了干哕,赵妈妈道:先歇歇,等会儿再吃。赵妈妈是过来之人,晓得是士英拣(音赶)嘴了,一会儿士英端起饭碗对赵妈妈道:她奶奶,水萝卜咸放哪块去了?忠仁道:现成的炖咸鱼不吃。今年的水萝卜腌得有些酸,吃粥都怕就着它。赵妈妈道:你不懂,酸儿辣女,这胎定是个小伙。赵妈妈端来水萝卜咸,递给士英,道:也指望是个小伙呢,不然你们心里不踏实,虽说有个文兵,给了别人,就是别人家的儿子。忠仁道:妈,你就不提那事了,都是自家兄弟。赵妈妈道:过两天你嗲嗲六七了,他们又回来了。又对忠仁道:大成子,他们晓得你嗲嗲多晚六七呀?忠仁道:晓得呢。赵妈妈道:你嗲嗲六七估计几桌客?忠仁道:估计三四桌。忠志道:最近上面有精神下来了,要移风易俗,不准搞封建迷信。赵妈妈道:做六七也叫迷信?忠志道:又换饭,又烧纸,还要放焰口念经,还不叫封建迷信?赵妈妈生气道:你当你的干部去,我们做我们的事。忠志道:上面要求党员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有专门工作组,明天就开始住到我们大队了。赵妈妈淌起了眼泪,用袖子抹了眼泪,说道:人死得了都没得安生。忠仁道:妈,你先别哭,听听忠志怎么说。忠志道:我就是不当这个主任,大队也不准办的,小则罚钱写检查,大则批斗进公安局。忠仁道:不能跟政策扛,你扛也扛不过去。老三忠礼道:老四是大队主任,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做也做不安稳。赵妈妈抹着眼睛,赌气撂下一句:随便你们。便去了锅屋,坐在铺沿上,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少不得儿子媳妇过来相劝一番。
到底赵广的佛事做没做成,下回接着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