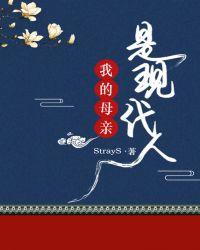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钓系美人被迫和亲后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沈怜枝心脏处的痛楚感愈发强烈,他哽咽道,「景策哥哥……」
「我不想和你分开。」
陆景策仍然沉默,可双臂的力道却加大了些,用力到怜枝几乎觉得骨头疼。
沈怜枝知道陆景策为他做了什麽,小安子都告诉他了,陆景策去跪了他亲娘,跪了太后,跪了皇帝。
外头的雪那麽大,他就这样跪了一天一夜,跪得人都差点冻死了。
但是没有用,事关大周与夏国,他们之间的那点情谊,又有谁在乎呢。
陆景策抬起头,冰冷的嘴唇在怜枝额上碰了碰。
他们安静地相拥片刻,然後陆景策抓着他的手,一步一步地走出门外,走向了皇宫的建福门。
沈怜枝在宫中默默无闻了十九年,如今人要走了,倒是热闹风光了一把,皇帝也亲自来送他。
建福门外站满了人,皆远远地望着盖了绣着龙凤团纹喜帕的怜枝上了婚辇,婚辇边上一众护送的护卫,还有骑着枣红色大马,充当使臣的鸿胪寺卿。
他仰头望了眼天,高声道:「吉时已到,启程——」
朱红轿子被抬起,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去,沈怜枝坐在轿子内虎口摩挲着自己另只手腕上的镯子。
已走出一小段距离了,沈怜枝忽然听到後头传来一阵喧嚣声,夹杂着华阳公主的惊呼:「景策?你做什麽!」
「世子殿下……世子殿下!」
沈怜枝盖着盖头,并不知道发生了什麽,只是轿子忽然停了下来,而後婚辇内猛然一沉,似乎是又有什麽人挤上来了。
下一刻,他头上的喜帕被人半掀起,还不等怜枝看清眼前景象,他的唇便被人堵住了。
用力的丶孤注一掷的丶似含着恨意的吻,胭脂的苦在两个人唇舌间弥漫开来,还有眼泪的腥。
吻他那个人一手紧拥他,另一手往他怀里塞了什麽,待他们分开後,沈怜枝才能看他面前的人——
陆景策握着他的手,贴在了自己冰冷的面上,他薄薄的唇好似勾了勾,只是眼中尽是哀伤与深沉:「怜枝,表哥无法看你行冠礼的样子了。」
沈怜枝低下头,这才发觉自己怀中揣着个极华美的金冠,陆景策说:「我本想在你及冠那日,亲手为你戴上的。」
「只是来不及了。」
沈怜枝难受得难以呼吸:「你别说了……」
陆景策俯身,又吻住怜枝双唇——又或不是吻,而是咬,几乎将怜枝的唇都咬破了,陆景策舐去那颗沁出的血珠,可怜枝唇上仍然留下一道伤。
他抬指在怜枝那伤上点了点,墨色的眸子直直地看着他,他叫他的名字:「怜枝。」
「你记住——你是要嫁我的。」
「怜枝,莫怕。」陆景策声音轻下来,「表哥一定带你回家。」
他还想最後吻一吻沈怜枝的面颊,只是来不及了,怜枝看到好几只手伸了进来,将陆景策拖下去。
沈怜枝抓住了陆景策的手,可对比起外头那些人,他的力气实在显得太渺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景策的手从自己掌心中滑走。
「表哥!」沈怜枝克制不住地泪流不止,「景策……」
分离的最後一刻,陆景策对他笑了笑,「不哭了。」
他被人带走了,轿子重新被人抬起来,沈怜枝盖好喜帕,眼前重归一片黑暗,心脏像是被人狠扎了一刀。
长安城中依旧在下雪,在喜庆的吹锣打鼓声中,送亲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里,送着一个心如死灰的泪人。
第3章斯钦巴日
从长安到草原大夏国几千里,随行队伍带着十里红妆,声势赫赫地往茫茫塞外处走。
沈怜枝在宫中再不受宠,到底也是皇子,身子很是金贵。这一路风雪无阻,怜枝可谓吃尽小苦,吃不下睡不好,已记不清吐了几回,人也瘦了一大圈。
约摸半月後,怜枝一行人走走停停地到了雁门关,此关隘居於大周与夏国的临界处,地处要塞,周遭群山巍峨,连绵起伏,很是雄伟壮观。
如今入了冬,下了雪,染得白茫茫一片,更是显得苍凉庄重。
小安子跳下马,掀开婚轿的帘子——一身红衣的沈怜枝睡在里头,他已偷偷地将喜帕摘掉了,整个人蜷缩在角落里。
只是哪怕睡熟了,眉头也紧拧着,怜枝菲薄的嘴唇轻微地翕合着,好像在说梦话。小安子将耳朵凑过去听了听,悄悄地听了半晌,才听清沈怜枝在嘀咕什麽。
「表哥……表哥……」
主仆连心,小安子听了,不知想到什麽,也是眼眶泛酸,他揉了揉眼,又将怜枝推醒了:「殿下,殿下。」
「……嗯?」沈怜枝做梦做得好好的,骤然被推醒,整个人还迷糊着,半睁着眼睛往小安子脸上看,「怎麽?」
「咱们到雁门关了。」
出了雁门关,要不了多久便能到草原上了。
沈怜枝揭了帘子将脑袋往外探,瞄了两眼,便灰溜溜地钻了回来。
主仆相对无言,一个唉声一个叹气,都晓得到了大夏国,日子会比在皇宫中还难过。
小安子哭丧着脸道:「也不知那大夏单于是个怎样的人,殿下,奴才听人说,草原上的那帮蛮子都是野兽变的,青面獠牙,可怕极了。」
怜枝也没见过夏人,只在儿时宫宴上遥远地瞧见过一个大夏使臣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