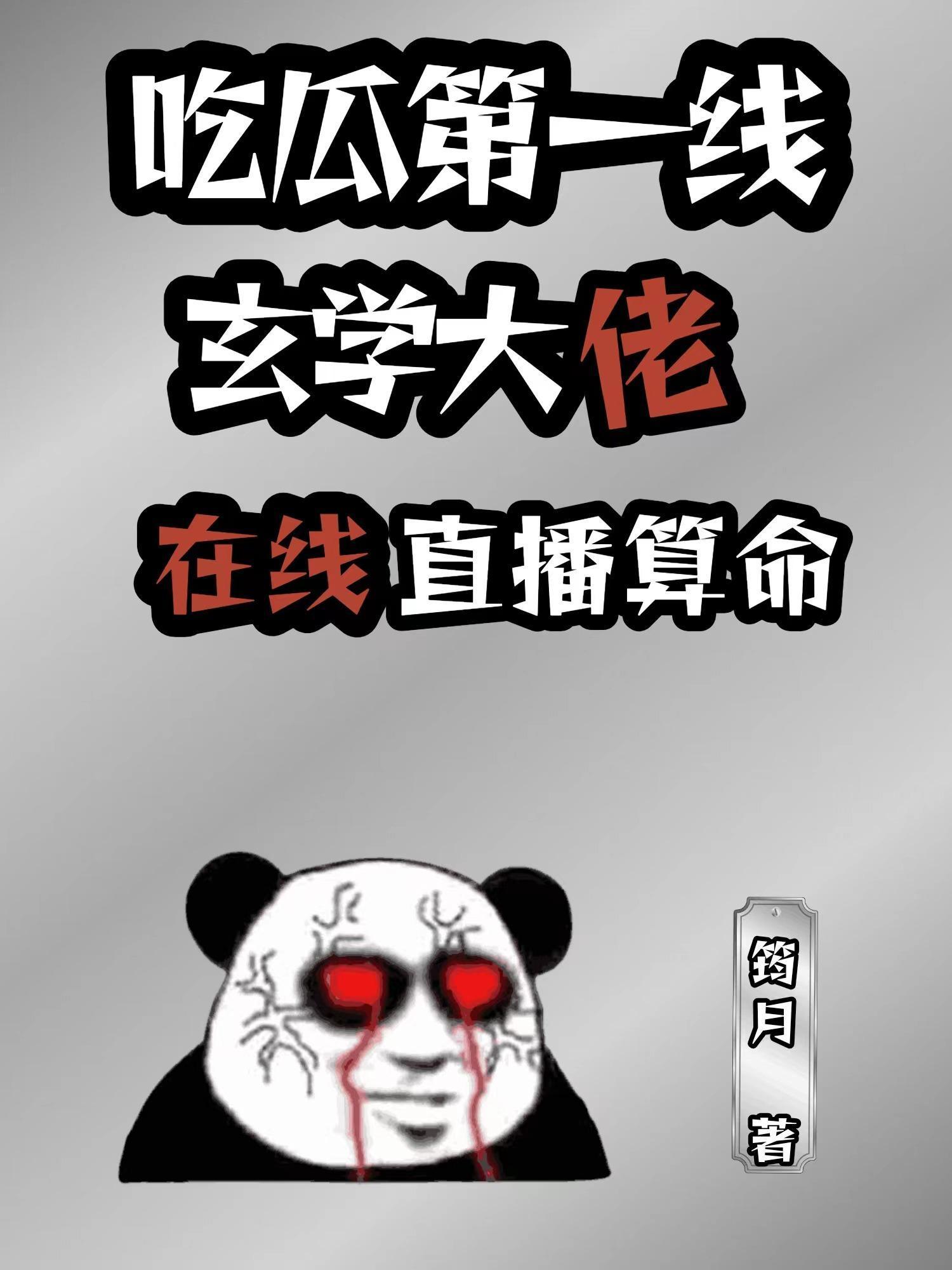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捡仙错金著 > 第56章(第1页)
第56章(第1页)
而他竟然不报仇,不恨她,还在为她做事,又算什么?
柳长年没法想,想不通,他是个武夫,从来没思考过这么复杂的事情,干脆只能不想。
他若是恨济善,就仿佛又推翻了自己似的,毕竟他之前那么挂念小善军师,还想着她有没有事,难不难过。
他还给她摘花啊!一腔热血,被她一箭钉得冰凉。
济善给他写信,令他们即刻从洛江回转,径直入青州,去城外拿那米粮做一个善事的幌子,好守株待朗。
她改变了计划,但依然把饼画的很圆满,给他许诺白山军的将来,许诺小将领的位置,许诺救出谭延舟。
济善认了许多字了,能够自己写信,把信写得十分直白通俗,有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就写什么,一点儿让人揣测的余地都没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显得坦然而亲昵。
还在信里嘱咐他管着一些何内雄与李尽意,又说,李尽意也不用太费心管,他是很野性的,烦了就随他去吧!
就好像他们是什么密友一般。
可是信里却对她当初射出来的一箭,一词不提。
柳长年很想问她,为什么?这算什么?你把我究竟当什么?
她一句不提,他想不通。
十来岁的少年,莽撞迷茫,行事多凭心性,要把一个性子诡谲的仙人弄清楚,实在的天方夜谭。
于是他只好强行不想,按照济善的示意,对朗星珠道:“郡主,有一话不知该不该说。如今郡主也瞧见了百姓过着什么样的苦日子,柳长年想斗胆问郡主一句,其余朗家人不管,你管不管?”
歹毒
济善站在太阳下打了个哈欠,拿着信对着光看。
她认字不多,而柳长年恰好是个武夫,二人一拍即合,把来往信件写得直白简单。据信中所说,柳长年已经以护送郡主的名义进入了城内朗府,但并未得到优待。
柳长年写道,朗星珠自己已经是自身难保,回到家中之后,先是与长兄大吵一架,之后又与病榻之上的朗正清大吵一架。
朗大骂朗星珠是个吃里扒外的赔钱货,朗正清骂朗星珠是个一无是处的蠢货,一家子骂得恨不能大打出手,把朗星珠气得从天黑哭到天亮,又从天亮哭到天黑。
朗星珠常年在外,早已与朗家脱节,被默认泼出去的水。她除了一张嘴和一个郡主的身份之外,什么也没有,故而在家中吵也是白吵,她回家一趟,如今已经近乎与家人闹翻,心凉到了要出门去浪迹天涯,或者出家当姑子的程度。
至于济善之前所说的,让柳长年通过朗星珠来干涉朗家这一打算,在柳长年看来,已经是完全落了空,不如早早另作打算。
而另一封信,是李尽意给她的,李尽意也不认识几个字,但他请人来帮自己写,以编故事的口吻,将身边的那两个大人给汇报了一番。
何内雄没什么可说的,他是实心眼,说赶路就赶路,说赈灾就赈灾,成日忙活着煮粥发粥,一身的饭味。
至于柳长年,李尽意认为他跟朗星珠两个是郎有情妾有意,马上要变成一对狗男女,抛下济善的大业滚去天涯海角厮混。他教唆着济善给他下令,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毒药,只要济善一声令下,就能立刻把这对狗男女送去魂归西天!
济善看笑了,李尽意像条野狗似的,只对她忠诚,其余时刻都在随时随地想着撕咬别人的血肉。这份极度排外的忠诚并没有引发济善的反感,反而让她想起陈相青身边的人,假若李尽意再大一点,说不定能与他们相抗衡,也免得自己事事亲力亲为。
她学陈相青,学他的姿态,学他的本事,学他的派头,自然也很想象他一般,能够有数不清的手下为之效力。
念完信,她默默地一口一口把手中信件吃掉。
千里跋涉而来的信纸之中,蕴含着风沙的气息,有人的气息,畜生的气息,以及那她不曾涉足过的青州的气息。
济善吃完信,扭头转过身来,平静地问:“我们在水和县所为,是谁透露了消息?”
地上跪了一列当初与她同去水和的粮官。
他们被五花大绑,一个个把头摇的如同拨浪鼓。
济善叹了口气:“你们也不怕我,怕他,怕李哲。”
麻子在左侧,其余人是跪着,他干脆是躺着,从头绑到脚,一双眼睛瞪大了,脸上的疖子抽动着。
济善看了他一眼:“我以为最起码你会同我站在一起。”
麻子嘴被布塞着,一句话说不出来,只能瞪眼。
谁能想到?谁能想到?!
麻子只想着东窗事发,这女人未必能保自己,于是自水和县回来之后,他便一直琢磨着自救。到了这个时候么,自救,自然是只能靠出卖自己人,来一个“我都是被逼的”
和“都是那个女人的主意”
。
谁知他打定了这个注意,才惴惴不安地怀揣着一肚子打算泼给济善的水出了门,临到上司家门口时,突然被几个汉子半路截道,打昏了绑来此处!
现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麻子一睁眼,见当初那一行人全被济善绑来此处,当即是想起济善在水和县杀人之时,心里凉了一截。
济善见谁都不愿意对自己说实话,于是走过去扯开了麻子口中的布,轻声道:“那么,你来说,你觉得当初是谁出卖了咱们?让我筹备的三百斤都打了水漂?”
“你知不知道,还有粮没来得及运出去,就被乱匪截了道,运到路上未出黎州的,阿黏也同我传了消息,说被歹徒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