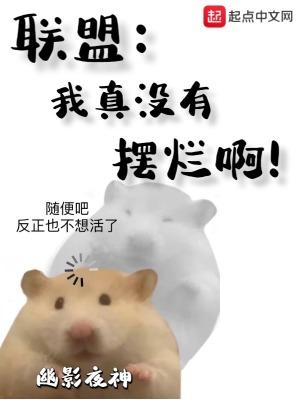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大河守望 关源岭 > 第二二三章 有个女子被贩卖(第1页)
第二二三章 有个女子被贩卖(第1页)
黑蛋像驴子一样拉着一车沉重的湿蒲草,他的心情比蒲草车子还要沉重,吭吭哧哧一步一个脚印向村庄走去。
他是要把湿蒲草拉回家,在院子里晒干缮房子用。蒲草是够了,还差一车子茅草,他得抽时间再到沙土岗上割一些茅草晒干才行。缮房子单纯用蒲草不行,虽然蒲草的保温性能比较好,但隔雨必须用茅草。要想又保温又隔雨,缮房时就得先铺上一层干蒲草,在干蒲草的上面再铺上一层干茅草,最后盖上一层和好的黏糊糊的黄土泥巴就行了。这样的茅草房冬暖夏凉,比瓦房住着舒服。尽管如此,但富裕人家都愿意住瓦房不愿住草房。因为住草房很麻烦,就拿黑蛋家的那两间草屋和小厨房,每隔三四年就得把旧草扒掉缮上新草,要不然下大雨或连阴雨屋里就会滴水。住茅草房的人家多数是因为穷盖不起瓦房,瓦房与草房在老百姓眼里是富裕或贫穷的象征。
当黑蛋吃力地拉着车子,走出黄河滩那一大片稠密的蒲草丛,光脊梁上像刚洗过澡一样流淌着不少汗水,感到浑身痒痒的不是滋味儿,他想擦擦汗喘口气儿,停下车子用汗水沁得半湿不干的破上衣,胡乱抹了抹脸上、身上的汗水,站着又不由自主地向黄河南岸茫然地张望,好像他想努力看到白菊居住的村庄,更盼望能看到白菊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他希望看到的倒是没看到,却看到了他不希望看到的。
他看到离他不远一群雪白的鱼鹰,在一个水坑的上边叽叽喳喳像乱箭一样上下翻飞着,好像水坑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这些水鸟。
黑蛋感到好奇,就皱着眉头向那个水坑走去。当他走到水坑的跟前,一股难闻的鱼腥味儿迎面扑来。他看到这个不大的浑水坑里熙熙攘攘游动着数不清的小鱼儿,大多是小鲇鱼儿和小鲤鱼儿,看不到一条大鱼。这些小鱼儿在浅浅的浑黄得像稠糊涂一样的泥水里,露着小小的脑袋、张着小嘴儿呼吸着,水坑里的泥水很难满足它们维持生命的需要了。
这个小水坑是黄河的浪涛猛然冲上了河滩又猛然退了回去,就留下了一个不深的死水坑,是浪涛把小鱼儿带到了水坑里,经过一些天的太阳蒸水坑里的水就越来越少了。这些小鱼儿都处在缺氧状态,即便不被水鸟吃掉,过不了三五日水坑的水就会干涸,这些鱼儿的命运可想而知。
黑蛋皱着眉头难心地看着这些小生命,扬起手臂“嗨嚎!嗨嚎!”
吓唬那些叨食小鱼儿的鱼鹰,可这些水鸟并不害怕,仍然毫无顾忌地叼起一条条的小鱼儿咽进肚里。
黑蛋无奈地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些小生命真是可怜……要是有一副水桶就好啦……把这些小鱼儿担到村里的水塘里,迟个两三年就长成了满水塘的大鱼了。”
他触景生情地叹息了一声说道:“人的命运就像这些小鱼儿,说不定浪涛啥时候猛然就把人儿甩到了死水坑里了,想逃出这个死水坑难上加难,只有听天由命。”
这时从远处忽然隐隐约约传来几声怪里怪气儿的吆喝:
庄稼长起来了嗨……
羊儿不能随便蹿了哎……
蒺藜扎住俺的脚了哟!
老母羊要下羔了吔……
黑蛋听了苦笑着说道:“一准儿是放羊娃儿小扁豆儿在胡乱咋呼。”
他接着叹息道,“像小扁豆儿这样不知忧愁多好!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黑蛋继续茫然地向黄河南岸遥望着……也许他明白他的眼睛是看不到黄河南岸的,是看不到白菊住的村子的,更看不到白菊。他的遥望其实是一种不由自主下意识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并没给他带来丝毫的安慰,反而增加了他不少的纠结忧愁。
他渴望见到他不断思念的白菊,这种对白菊的绵绵思念与对白菊难于猜测的变故,像一张黏糊糊的网笼罩在他的心头,使他心中产生的意念也变得黏糊起来。
这一段儿的黄河离黄河南岸加上流水与不流水的浅滩大约有五华里宽窄,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模模糊糊的对岸像一条灰色的长布条,对岸的树木影影绰绰的时隐时现,村庄与房舍连个影子也看不到,整个黄河南岸像被一层薄薄的细纱布轻轻覆盖着,更难看清对岸的人或动物。
黑蛋明知道他的盼望难于随愿,也知道这种期盼的是徒劳的,虽然这种徒劳的期盼给他带来的是苦酸的失落,但他无法控制自己。
他甚至奇怪地感到对岸有点儿神秘莫测,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于猜想的秘密。觉得黄河南与黄河北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不知道黄河南的人们与黄河北的人们有啥不一样,风俗习惯有啥差别。他想动脑子琢磨一会儿,他瞪着大眼望着天空,只见天空中不断有飞鸟的影子,他又沮丧地闭上了眼睛,仰脸叹了一口气儿,握着拳头使劲儿地朝他肌肉达的胸脯上捶了一下,毅然吃力地架起了车子。
当他架起车子,正准备踏上归途的时候,忽然看到黄河里顺着北岸河边缓流驶来一艘小船。这艘小船顺水向东晃晃悠悠慢慢行进着,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凄凉与孤独。隐隐约约间,黑蛋似乎听到船上似有女子的哭声,那悲切而绝望的哭泣声穿透空气,直击他的心扉。他急忙停下了脚步,眼睛紧盯着那缓缓行进的木船,不由自主地跑向河边观看。
他将那女子的哭声与心中深深思念的白菊奇怪地联系起来,尽管他知道船上哭泣的女子很可能是与白菊无关的另一人,但他还是心怀忐忑地想看个究竟。或许,这份关注源于他对女性的同情与尊重,也或许,是那份对逝去恋人的深切怀念让他变得格外敏感和多情。
当黑蛋看清船上的情形时,他的心头不禁一沉。船上有三个活人儿,一个男子汉正在卖力地划着船桨,另一个男子汉则叉腿掐腰,摇摇晃晃地站在船板上。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名年轻女子,她被绳子捆绑着手脚,半躺在浅浅的狭窄船舱里。她不断踢腾挣扎着,试图摆脱束缚,但无济于事。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无助,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