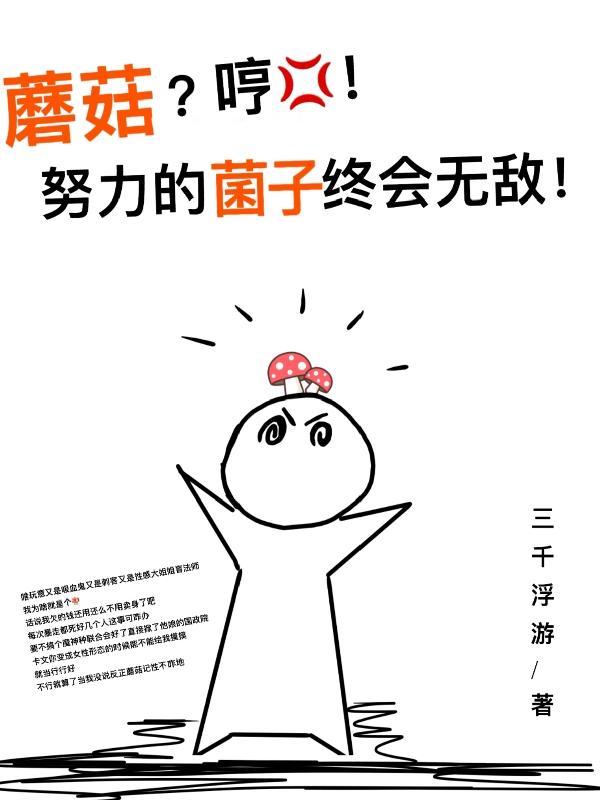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地府小死亡是什么技能 > 第81章(第1页)
第81章(第1页)
梵筠声拖着椅子,离得更近了些。
“我是给你吃哑巴药了吗?一见我就不说话,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闷在被子里的迟何:“没有。”
“那你就是对你自己有意见。”
梵筠声一手抵住他的肩头,将他半边身子侧推起来。
里衣之下是几圈绵密的纱布,这纱布颜色很白,在米白色里衣的衬托之下十分显眼。
更显眼的是纱布上正在往白处扩散蔓延的鲜红。
“我们在地府的身体是不会流血的。除非魂魄受伤,或者神魂动荡。”
或疯或伤。
梵筠声扫了一眼,确定这纱布只缠绕在上半身后,便将迟何扶了起来,避开伤处,让他靠在侧墙边。
“六阎殿大人,你可别告诉我你是赶工单赶疯了。”
迟何淡淡地抬眼看他。
梵筠声:“那我会说,疯了好啊,终于疯了,都一千年了我就等这天呢。”
换别人早疯了,就你迟何能憋。
迟何听见这个“一千年”
,忽然低笑了一声。
“一千年这样算下来也不是很久。”
他只杀了那个人五十几次,比他预想的少很多。
梵筠声仿佛看穿了他,问:“你在算什么?”
“算轮回。”
轮回梵筠声迟疑道:“你是在人界受的伤?”
这是一个全凭直觉的提问。那些一闪而过的片段和话语凑在一起,他突然就想这么问。
迟何滞了下,下意识想遮掩,但又觉得事已至此,没有必要。
“不是。但我的确去了人界。”
伤不是在人界伤的,但也有点关系。
梵筠声又道:“魂归日前后,你在辂庄?”
“对。”
“你去那里做什么?”
迟何就任六阎殿,那都是一千多年前的事儿了。就算有什么未了前尘,也早该过去了。
“讨债。”
讨一个按理来说早就还清了的债。讨一个只有他仍然耿耿于怀,且永不会和解的债。
梵筠声忽然有点怜惜地看着他。
“一个债记了一千多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好像能理解你拼命赶单的原因了。”
迟何摇摇头,“不必费心讨我开心,有什么想问的,便问吧。”
好吧。开心至上的七阎殿不但没能讨人开心,自己也有点沮丧了。
他看向迟何的后背,“不是人界,那便是厉刑司?”
“纱布缠绕的面积如此之大,是剥皮之刑?”
他好像找到了真相,“你你和芙倾打过照面了?你背上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