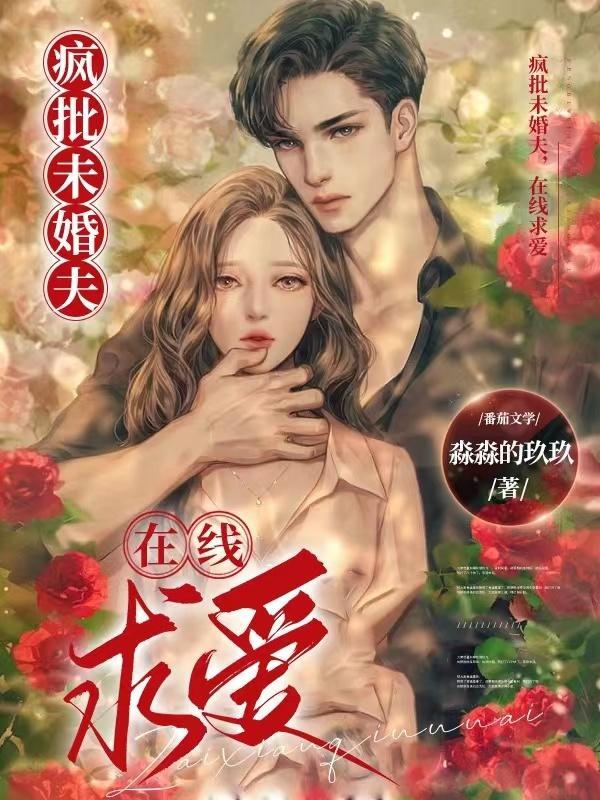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我又没让他喜欢我[星际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低烧的克里琴斯迷迷糊糊地想。
腰背又疼起来。
克里琴斯指挥他说:“我腰疼,腿疼,你给我揉揉。”
炽树怔住:“啊?”
克里琴斯:“你还不乐意干活了?是谁害我腰疼的?”
炽树颇有点受宠若惊:“我、我可以碰你吗?”
克里琴斯难以理喻地说:“又没有脱衣服,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不准想!”
克里琴斯翻身趴下,让炽树给自己按摩。
炽树心惊胆战地上床去,不敢压在克里琴斯身上,动作笨拙地给他揉腰。
闭上眼睛的克里琴斯看上去整个人颜色淡了许多,他的色是白色嘛,唇色也淡,眉毛睫毛也是。
克里琴斯的床铺的真丝床单,看上去柔软华贵,上次好像是米色的床单,这次是深紫色的,反衬得他像是紫蚌中的一颗雪白珍珠。
炽树小心翼翼地揉,这腰肢这么细,尽管覆着薄薄的肌肉,但他还是有种怕一不小心被折断的错觉。
克里琴斯皱着眉:“你力气也太轻了,今天你不是很有力气吗?用完了?现在没力气了?”
炽树哄说:“宝贝,我还是轻点吧。”
“?”
克里琴斯,“你再说一遍?你刚叫我什么?”
炽树:“……”
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口了。
被克里琴斯白了一眼。
克里琴斯转过身,指着他说:“不准用这么肉麻的词称呼我,再说了,我们又没有那种关系。”
“算了,不用你了,我药也吃了,水也喝了,你走吧。”
“不用一直陪在这里,要是有事的话,我会叫你的。”
他就这样,对炽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而炽树居然也不恼火,乖乖下去,站在床边:“我不能留下来照顾你吗?我保证,我什么都不做。”
“难道你还想对我做什么吗?”
克里琴斯警惕起来,“你在边上盯着我,我怎么睡得着嘛。”
看来,只能先离开了。
炽树心有不甘,说:“我再给你量一次体温,要是降了我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