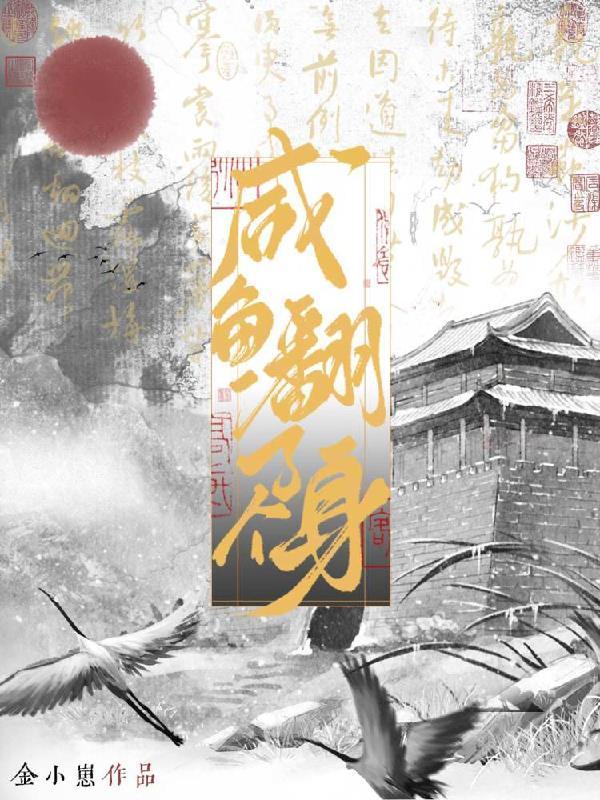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旺妻命什么意思 > 第18章 话里真真假假谁搞得清(第2页)
第18章 话里真真假假谁搞得清(第2页)
“我怀疑他们压根儿就没种任何东西,草肯定是自己长出来的,然后怕我闹,骗我说种了草。”
“他们有必要这么骗吗?”
荣雅香问。
蔡泽的眼神像凝固在那里的探照灯,死死地盯着房雪怡。
房雪怡显出谁也骗不了我的精明神态:“野草可以喂猪呀,又省力又赚钱不是?”
荣雅香松了一口气,深表同情地说道:“哎~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谢夫人的地多的是,你干嘛非选皮家村的地?”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兄长那德行,他会给我好地吗?他给我的肉铺也惨淡得不得了,幸亏琼娘子看在我娘以前帮过她的份上,愿意照顾我生意,否则我只能关门大吉了!”
“原来如此。”
“接下来我想去皮家村问那租户买猪。他欠我钱,自然猪得便宜点给我
才是。”
房雪怡故意说道。
“别——”
荣雅香脱口而出,但是马上改口,“我是说。。。。。。我猜啊,皮家村进贼了,租户手里没钱,肯定盼着猪卖高价,定然不肯便宜。”
“不去问怎么知道?”
“我让人帮你问一声便是,免得你自己去跑。”
荣雅香主动提出。
“也行,那快点给我消息,我马上得进货。”
“没问题。”
太叔幸生悬着的心落下来,房雪怡看上去冒冒失失的,其实心思挺缜密,说出的话挑不出毛病。
荣雅香阻拦房雪怡去皮家村,说明知晓皮家村里的秘密,所谓的还钱宴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蔡泽想进一步试探太叔幸生,主动给太叔幸生敬酒:“我们也算是有缘分,贤弟。。。。。。必陌贤弟,敬你一杯。”
反应迟钝的太叔幸生赶紧站起来,双手举着杯子,一副感激的模样。
房雪怡立马把杯子抢了:“有点骨气好不好,跟渴死鬼似的,前生前世没喝过酒吗?非得在这里喝!”
明显还是十分排斥蔡泽的。
蔡泽尴尬地说道:“是我的错。我只是想——”
“你敬酒有错吗?”
荣雅香不满地插话,“这位姑爷喜欢喝酒也没错。打猎的喝酒是为了壮胆取暖,哪个不好酒?雪怡你别总是那么霸道,连酒都不准人家喝,好像他其实喝不了酒似的!”
“谁说他喝酒不行?他在家里经常偷酒喝,醉了就耍横,拿我后院养的鸡
当猎物打,真是受不了他,不能让他在这里贪杯!”
太叔幸生担心不喝酒骗不过蔡泽和荣雅香,强行抢过酒就倒进嘴里。
然后砸吧着嘴,舔着唇,似乎不解瘾,手握着空酒杯不放,眼睛盯着酒壶。
蔡泽看出太叔幸生还想喝,又给他倒一杯:“来,我们不醉不归。”
房雪怡气得拿起钱袋子就走:“臭男人,你要喝就喝死在这里,有种别回家!荣大小姐,我先走一步,等你皮家村的消息,要快点哦。”
太叔幸生哪敢,连忙对蔡泽歉意地笑,放下酒杯牵了狗急吼吼地去追房雪怡。
门刚关上,荣雅香的脸就刷下来,冲着门骂:“呸!一点教养也没有!瞧瞧他俩,一个是泼妇,一个是孬种,真是绝配!”
蔡泽闷不做声地喝着酒,没有搭话。
房雪怡的性格他了解,爱也分明恨也凌厉,待人不是黑就是白,没有逢场作戏那一套虚伪。
她待人好的时候其实通情达理、温柔贤惠。
现在变成这样,那是因为她记仇。
荣雅香靠近蔡泽,搂住他的手臂,声音嗲嗲的:“蔡郎,你帮我判断判断,刚才有关皮家村的事,房雪怡有没有撒谎啊?”
蔡泽摇摇头。
他从不怀疑房雪怡。
在他心目中,房雪怡是根直肠子,什么都写在脸上嘴上,瞒不住什么事情,所以压根儿不会撒谎。
他之前一直怀疑的是太叔幸生,怀疑他并非什么流民,而是寒鸦卫,利用了房
雪怡单纯的感情落户黔城查案。
可是经过多日观察,他发现太叔幸生除了跟在房雪怡身后,从不单独出门,不像一个探子。
今日仔细考察,太叔幸生作为哑巴没有可疑之处。
此人纯粹就是个漂亮的花瓶,行为举止却是个点头哈腰的粗鄙猎户德性,而且贪酒又惧内,没啥出息。
解除了对太叔幸生的怀疑,蔡泽决定马上实施第二步计划了,以免夜长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