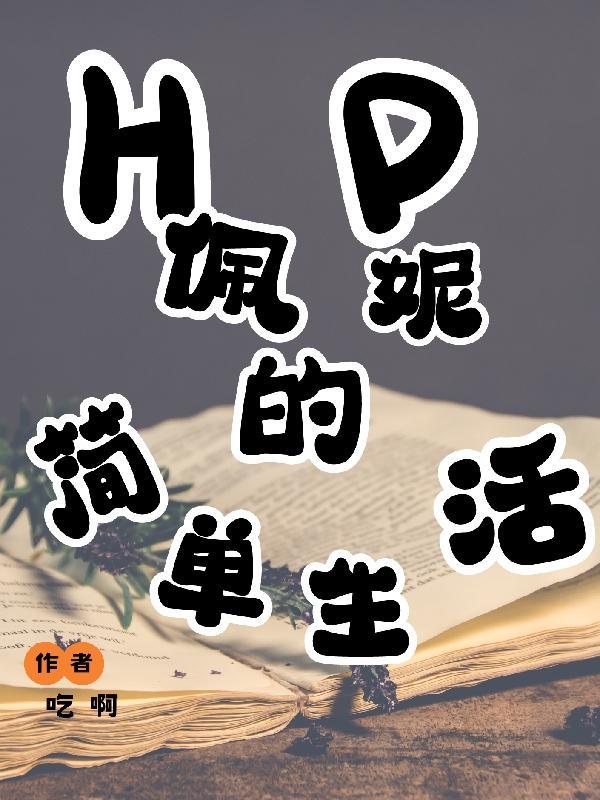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漂亮小少爷又要被罚了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时淮一天比一天憔悴,正以一种很快的速度逐渐凋零,却仍咬着牙坚挺着。
几天前为了拿到一份六年前的合同甚至被几个由应祈年牵线才答应与他吃一顿饭的老总灌酒灌到了天昏地暗,还是他跟许知会及时赶去才将人带了出来。
“阿淮,你能别这样吗?”
许知会实在忍不了了,看着眼前喝到醉醺醺的青年,皱了皱眉。
“应……应祈年说了,多一份证据,盛……他就能多判几年……”
时淮双眼醉意朦胧,扬了扬手中被酒液沾湿了一角的合同,脚步踉跄了一下,被边浔架住了胳膊。
“然后……然后小岛,小岛就能回来了……就不会,不会被欺负……”
时淮显然意识已经不清醒了,却仍在含糊不清地呢喃着。
“……”
边浔一语不发,只不露痕迹地叹了口气,伸手拂了一把时淮额前被酒液沾湿而凌乱不堪的碎发,拽了好几下才接过他手里那份攥的很紧的合同。
“别什么都靠自已,阿淮,下次叫我们一起。”
沉默了很久,边浔才直视着那双通红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对,对,叫上我们,我至少酒量好,喝不倒,别什么事都自已扛着。”
许知会说着,扶住时淮的另一只胳膊,两人架着青年上了车。
一路上,寂静的车厢中只有一个微弱又沙哑的声音一刻不停地喊着小岛的名字。
边浔开着车,手指攥的很紧,指尖都快要陷进方向盘里。
许知会则转头望向窗外,眼眶微微泛红,一刻都不忍再听下去。
……
时越山是在第二天中午醒过来的,竭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的那一刻,他一眼就看到正垂着头坐在床边,将整张脸都掩在手掌间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也是他很久没有见到的身影。
“阿……阿淮……”
他的嘴唇在呼吸面罩下蠕动着,艰难地发着气声,在面罩上呼出了一片雾气。
时淮猛地抬起头,眼睛红的跟兔子一样,像是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过觉。
他在看到时越山醒来后先是怔愣了一瞬,紧接着摁响了床头的铃。
刚查完房的边浔闻声带着护土匆匆赶来,认真检测仪器上的数据,测量心率和血压。
“时叔叔,您就安心养病,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边浔俯身轻声说道,紧接着望向时淮,朝他点了点头,然后与护土一同走了出去,将空间留给了时越山跟时淮两个人。
时越山仍在不停地呼唤着时淮的名字,眼角有浑浊的泪珠滚落下来,洇湿了一小片脑袋下的枕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