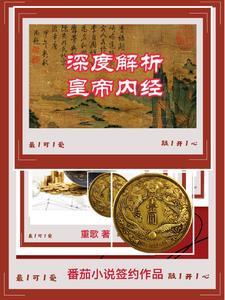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嫁寒门将军做主母 土金戈 > 第42章这把老骨头也不怕摔着(第1页)
第42章这把老骨头也不怕摔着(第1页)
“老奴是翠兰街卖豆腐的,儿子叫周达,老头子叫周来兴,一月前没了。”
老婆子身着破布,立在最后头,垂着头说话。
“老子才死,儿子就要卖娘?”
裴仪瞧着拈酸的老婆子,脑海里想象着周达卖娘的场景,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气。
“不是的,不是的!”
老婆子连连摆手,涨红脸,着急解释,“不是我儿要卖娘,是我的主意!”
说着老婆子眼红,擦泪说:“老头子没了,豆腐行情又不好,儿子还没娶亲,我老了,不中用了,哭着求我儿子卖了我。先不说我能不能攒下钱来贴补他,但说卖我的几两银子,也够他娶个媳妇。”
也是这般寒酸。
裴仪想起过世的娘亲,倘若崔涟漪还在世,兴许她的日子,没那么难过。
“为母则刚,老母亲为儿子考虑的如此长远,希望他不要辜负了你。”
裴仪安慰老婆子,“周达娶媳妇了吗?”
“还没。”
裴仪思虑一转,她正巧没小厮可用,若是周婆忠心,做事利索,发展发展周达,也不是不可。
心里盘算,嘴上说:“先叫他别娶,等日后我给他说一门亲。”
周婆面带喜色,忙下跪叩头:“老奴谢姑娘大恩大德,日后肯定好好孝敬姑娘!”
“这把老骨头,你也不怕摔着,快起来。”
嘴上这样说,但裴仪的身子却一动不动。
该有的话有,但是该有的威严,她也要有。
皂白机灵,连忙扶起周婆。
秋子知道裴仪认可周婆,遂在花名册上登记。
“如此,咱们院里的人齐了,我也识得,让秋子同你们讲讲各人的活计。”
秋子放下笔墨,起身,走到廊前,朗声对众人说。
“皂白和丝萝是大丫头,留在屋里,近身伺候。你们二人轮番在屋里上夜,监察火烛,铺床摆褥,摆理饭食,伺候姑娘梳洗,打扫卫生,姑娘屋里的各桌各椅,瓶罐字画,痰盂扫帚等,皆由二人管理。可听清楚了?”
“回秋子姐姐,奴婢皂白,听清楚了。”
“回秋子姐姐,奴婢丝萝,听清楚了。”
两人齐声回答,裴仪甚是满意。
“余下五人,皆是粗使丫头,你们不用因自己是粗使就不用心做活。往后姑娘出阁,少不得你们跟过去,将来做妾,还是在姑娘爷们跟前伺候,都是你们的造化。姑娘的日子过得好,你们的日子自然好,寻一小厮嫁了,或给侯爷伯府什么的做通房,日子也能安稳。”
秋子知自己话过,悄悄瞄裴仪,见她没说什么,把话题拉了回来。
“粗使和周婆负各类粗活,各屋院的卫生,冷热水的供应,往来的饭食,虫草花卉的打理,衣裳的浣洗等等各类,只要是姑娘吩咐的,大丫头传话的,你们都要用心的去做。听明白了吗?”
“奴婢明白。”
五个粗使丫头和周婆,一并回答。
裴仪见规矩讲得差不多了,是时候收尾,于是一面摆弄指甲,一面端详众人,一面状似柔声细语,却厉道:
“各人的职责众人都明白,咱们院里各类物件儿,或丢或丢,或懒惰,不愿做事的,或好吃好喝,偷吃偷拿的,或打架拌嘴,勾心斗角的。若叫我知道了,该打该罚,还是怎么,我前头说过,各自去悟去。可还有不明白的没有?若现在各位不愿在我屋里当差的,只管明说,咱们好散好聚,若后头办事不经心,好聚可就不好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