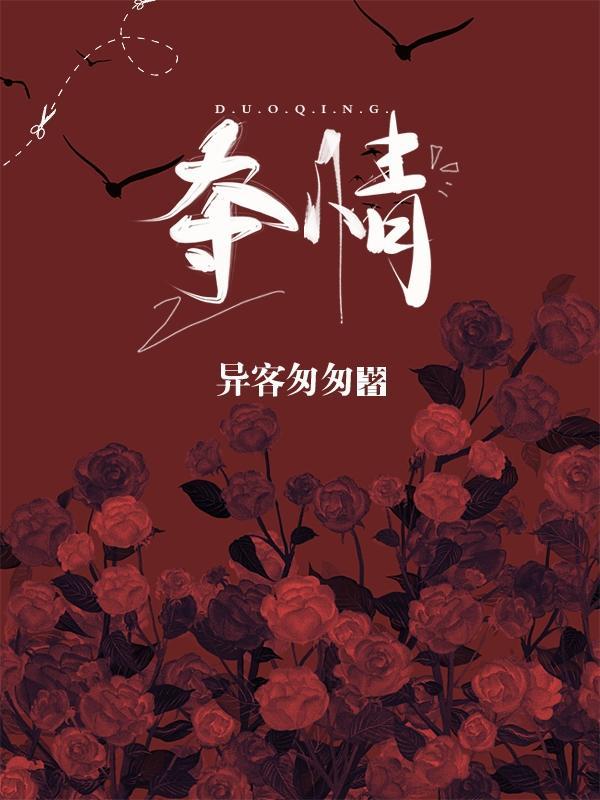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朕靠宠妻续命30章 > 第23章(第2页)
第23章(第2页)
幕七被他这一笑晃了眼,只觉指尖皮肉被包裹的一点热意一直烫到心底,一时忘记抽出。
“但是吧,朕交朋友,一向都遵守一个规矩。”
雍盛狡黠地眨眨眼,“叫做礼尚往来。”
幕七直觉不妙,刚想挺腰起身,雍盛已趁他一只手被控住,另一只手飞快地扯下他的腰带。
他倏然瞪大了眼睛。
“是吾友就别挣扎,听话。”
雍盛耀武扬威地抖落那根玄色腰带,如一只趾高气昂骄傲的小公鸡。
什么规矩云云,写作礼尚往来,读作以彼之道还治彼身。
幕七不禁莞尔,已猜到他想做什么,认命地闭眼。
雍盛见他不等自己用腰带蒙他眼睛,就先一步闭上眼,倒是惊诧了一把,嘟囔道:“这么信我?”
他当然知道被剥夺视力是什么感受。
那种不安与恐慌,会于无边的黑暗中自内心深处疯狂涌出,无助感淹没神识,迷茫铺天盖地,除非身边的人是极其信任之人。但谁又定然料得准,你信任的人是佛,还是魔?
他一个健全人尚且如此,换作又聋又哑的幕七呢?
他们不过萍水相逢,此时他耳不能闻目不能视,雍盛如欲下毒手,他身手再好又如何?
还不是俎上鱼肉任人宰割?
由此可见,此人对他全然信任,确无歹心。
尽管雍盛自己也不明白,他对自己无理由的信任,从何而来。
试探过后,雍盛彻底放下戒备,却仍坏心眼地将那根腰带覆上幕七的眼。
“这下好,也教你尝尝当瞎子的滋味。”
雍盛知他听不见,便躺下了自言自语,“朕亲爱的九皇叔此时定在外头寸步不离地替朕守大门呢,真是感人肺腑。”
他略带嘲讽地扯了扯嘴角:“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此话不假。你这么能算,是不是也算到我会搬来雍峤这尊大神?怕是不能吧?”
他自问自答起来,也不再使用“朕”
这个自称。
“其实我也是赌,赌雍峤不会坐视不因为一旦我在这里遭了老王的毒手,按规矩,这皇位就得顺着传给雍昼,无论如何也到不了他手里。他那份暗室之谋处心积虑了少说也有五六年之久,这些年来招兵买马,收拢人心,劳神靡费,怎能眼睁睁看别人摘得胜利果实?所以按顺序,他得先斗倒雍昼和王家,才能接着跟我斗。我要是死早了,对他可太不利了。唉,不过今天我还是失算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到头来还是白折腾。你说,这书里原有的剧情是不是真的避不开,要真是这样的话……”
笑
他琐碎地咕哝着,直到睡去。
也就睡了一眨眼的功夫,尚未摸到周公的脚后跟,就有人在耳边喋喋唤。
“圣上,丑时初了。回宫后还得沐浴更衣,再晚就误了朝会时辰了。”
雍盛勉强将沉重的眼皮掀开一条细缝,觑见身穿常服的怀禄,先是愣了一瞬,再回去摸床上,摸了一把空气。
“幕先生与缃荷姑娘已先走了。”
怀禄扶起雍盛,欲伺候宽衣。
㏄㏄
雍盛仍闭着眼,抱紧了被子不撒手,用鼻音哼了一声:“王炳昌没拦他?”
“是九王爷亲自将人护送出的府。”
怀禄道,“奴才昨夜为免教人瞧出破绽,将圣上的随身玉佩交予王爷后并未与王爷一道前来,直在外头等到三更天,实在忧心如焚,这才叩门进府。进来的时候恰巧撞见二人离开王家,瞧样子,缃荷姑娘似与九王爷是旧识。”
【】
“哦?”
雍盛冷嗤,“幽蘅院的业务倒是做得广。”
说着仍是不动,极不情愿地延挨片刻,才在怀禄一声又一声的催促声中挣扎起身。
时间紧迫,怀禄伺候雍盛更衣净面,再由王炳昌陪同,雍峤领亲兵护卫,乘轿赶往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