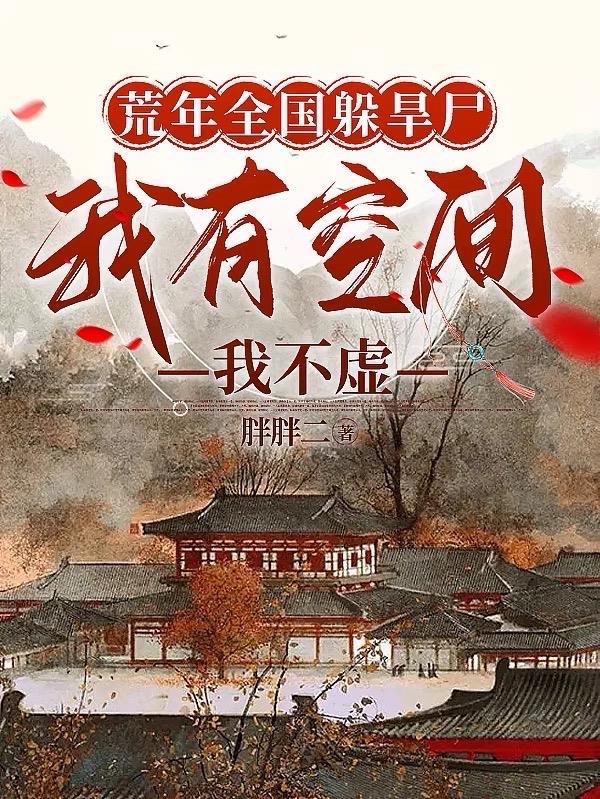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攻略病弱反派的正确方法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焦成难得露出笑容:“是。”
裴醉擦了把汗,压低嗓子:“别让申行借清纶教造反的名义朝梁王下手,也不能让他调兵出城。”
焦成略显犹豫。
“击鼓鸣冤,聚众闹事,士兵哗变,会不会?”
裴醉瞥了他一眼。
“是!”
焦成摩拳擦掌,扭了扭脖子,鹰隼一般的目光在黑夜中烁烁。
他当了那么多年捕头,也没能把望台变成人间正道。
既然如此,诡道又何妨一走?!
“去吧。”
裴醉扶着城墙上的泥砖,略一垂头,冷汗便从鬓边滚了下来。
焦成没犹豫,扶着腰间厚重细长的铁尺,便没在黑夜里。
陈琛此时哪还敢骂他病秧子,心疼地差点给他跪下:“殿下,你不舒服?”
“别废话。”
被骂的陈总河官挠了挠头。
刚刚梁王殿下,可不是这种待遇。
邓卓紧紧握着手中的拐杖,朝裴醉低声道:“大帅,末将或许能帮上忙。”
裴醉抬眼看他,思索一阵。
“天字所掌火炮,若是堤坝人为损毁,你确实应该能看出来。”
“是。”
邓卓垂着头,右手攥得很紧。
裴醉转头望着遥遥内城,抿着唇,从怀里掏出‘裴’字令牌。
“玄初。”
唯一一个不肯听话的,就是这个硬脾气的玄字首领。
就算他下了死命令,玄初也不肯离开他半步,就算下午刚领了二十军棍。
“主子。”
玄初从裴醉身后缓缓走了出来,黑巾遮脸,只留一双狭长的眼睛,眼尾一颗小痣,如一滴泪。
“拿着我的令牌,去调驻军一万人,围城,剿匪。”
玄初重重跪在裴醉面前,双手捧着令牌,却不肯动。
“玄初绝不离开主子半步。”
“这是我欠他的,他一定不能出事。”
裴醉左手攥着玄初的肩胛骨,极用力,“你护着他,便是护着我。”
玄初双手紧紧捏着令牌。
“主子已经不能再受伤了。”
“我本来就活不长了,可元晦他还有大好的前途。”
裴醉声音渐低,“去吧,梅叔。”
玄初手一颤。
梅,是凤惜双赐给他的名字。
小主子还记得。
“是。”
玄初将令牌揣进胸口,右手攥着裴醉的手腕,狠狠一握,立刻松开。
“主子,千万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