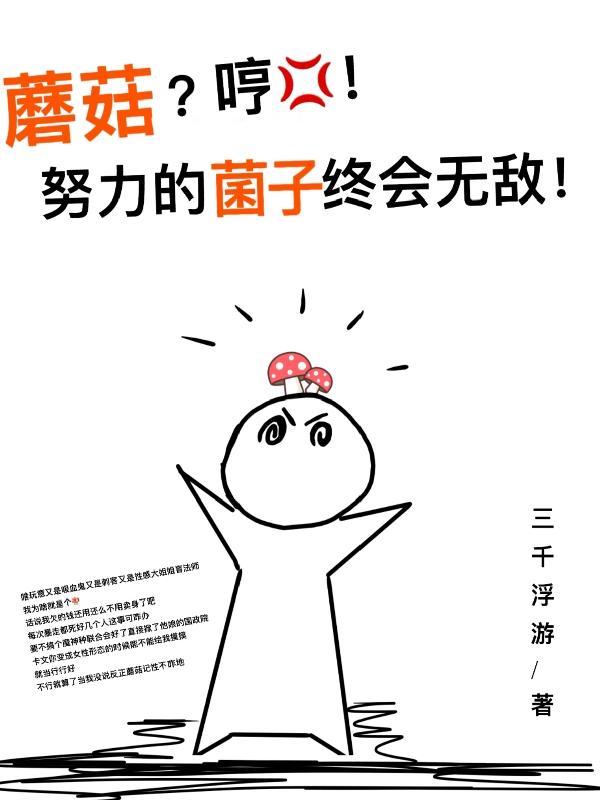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揽流光鹊上心头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她看了看薛皇后又垂下眼眸,犹豫着开口:“姑母昨日……为何向陛下为我求郡主之位呢?”
“阿玦是个聪明姑娘,”
薛皇后仍笑着看她,只是那笑意并不达眼底,“阿玦如何觉得呢?”
容玦头一次感受到了薛皇后身上散发出逼人的气势,她顿时有些害怕,缩了缩身子不敢直视她,只是垂着头轻声道:“姑母……姑母自然是疼惜阿玦。”
薛皇后这才真真切切地笑了起来,拉起她的手柔声道:“我们薛家只有阿玦一个女儿,姑母当然疼惜阿玦的。”
薛皇后的手十分冰冷,令她浑身一震。
容玦稳住自己微微颤抖的身子,故作天真般看着薛皇后,挤出笑着说:“我就知道姑母最疼我,阿兄常常说姑母对阿玦比他好呢,照我说他就是嫉妒姑母对阿玦好呢!”
“薛琮那个臭小子,”
薛皇后笑着摇摇头有几分无奈,她温柔地注视着容玦,“怎么比得上宝贝阿玦,阿玦就要及笄了,姑母一定要为阿玦找门好亲事。我们阿玦值得这天下间最好的男儿。”
容玦脸上适时浮上红晕,她挽上薛皇后的手臂,靠在她的肩头,一副小女儿娇羞的姿态:“姑母说什么呢,阿玦还小呢,想在父母和姑母身边多侍奉几年呢。”
“阿玦就是喜欢耍小脾气,”
薛皇后轻轻拂着她的脑袋,目光不知看向何处,声音却是上位者的不容拒绝,“阿玦享受这金玉满堂的生活,自然也会为薛家尽一份力的对不对?”
容玦甜甜地应道:“那是自然。”
薛皇后没能看到容玦染上冰霜的面庞。
“我听闻近日太子与柳家二郎有所接触,皇后娘娘也曾召柳家娘子进宫相伴。”
容玦沉在回忆里的思绪被牧平也清淡的声音拉出来,她托腮看着对方:“牧公子真是消息灵通啊。”
牧平也笑了笑没有回答,容玦也不欲多加纠缠,只是说道:“你我都能猜到皇后娘娘的意图,虽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只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还有一个崔家虎视眈眈地盯着。”
“况且,”
她盯着对方的眼眸,缓缓道,“吾不欲为棋子,欲为执棋者也。”
“姑娘这便是玩笑话了,”
牧平也笑意盈盈的,只是那笑却总让人无端想到冬日疏离的阳光,“在下不过一个小小掌故,怎会有如此能力?”
他微微倾身,看着她漂亮的双眸探究道:“姑娘本就是薛家人,我该如何相信姑娘呢?”
容玦笑了笑,上下打量了一番牧平也,悠悠开口:“公子能令大儒程耳侧目,必是有过人之处的。”
容玦不再多言,转而看着院墙上郁郁葱葱的地锦,忽然道:“公子看这地锦,爬得如此高,看着也甚是繁华。其实它十分脆弱,一场突然的暴风雨,亦或是它自身就能将自己坠下墙头。”
“毕竟高处不胜寒。我不希望它爬得太高太远,我只想它平平稳稳就好,”
她转首,神色平淡地看着牧平也,正色道,“我有我想保护的人。”
牧平也闻言心头微动,他知晓薛容玦聪明,但却未曾想到她竟如此通透。
“姑娘为何选我呢?”
他拿起茶壶,为二人各斟了一杯茶。
薛容玦笑了笑,她微微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间或有几只鸟儿飞过:“公子心中有鸿鹄之志,是要翱翔于蓝天之人。”
“我相信公子一定可以。”
她的双眸澄澈无暇,是不加掩饰的信任。
牧平也倒茶的手微微顿了顿,生活的锉磨已经让他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对人完全托付信任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他竟有些不敢接下这份信任,微微错开她的眼光,将茶杯置于她面前:“姑娘不怕我有私心吗?”
薛容玦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耸了耸肩显得十分洒脱:“谁人没有私心,说句冒犯的话,当今圣上开疆拓土自然是为了边境子民不再受北蛮人侵扰、为了天下安宁,但谁又知他是不是希望在史书上留下美名呢?毕竟,生前身后名谁不想拥有呢。
“私心与目的并不冲突,只要公子能坦荡面对自己的私心问心无愧,我又有何担心?
“我只担心自己能否说服公子。”
牧平也抚掌大笑,抱拳道:“姑娘心中有丘壑,在下心悦诚服。”
“谨以茶代酒,”
他举起茶杯,举手投足间竟有些名士风范,“愿你我夙愿得偿,待那日你我再饮酒相贺。”
落絮无声(七)
薛容玦的这场生辰宴办得声势浩大,远处水榭中的戏子唱遍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庭院里觥筹交错,桌上珍馐美馔。
对于薛家的繁盛,艳羡者有之、嫉妒者亦有之。薛皇后在生辰宴稍坐了坐便先行回宫,太子殿下仍留下为表妹庆贺。
薛容玦瞥见薛琮带着牧平也前往太子殿下坐前,向他引荐着牧平也。
远远瞧着,不知牧平也说了什么,太子拍着他的肩朗然大笑,二人不像浸染在权势朝堂中的人,而像那山中名士,举手投足间尽是风流。
周韫带着薛容玦在世家夫人间周旋一圈。
不少贵妇人都转着弯地打定薛容玦可曾定亲,都被周韫搪塞了回去。
毕竟她也知晓,薛容玦的婚事已经不是薛家可以做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