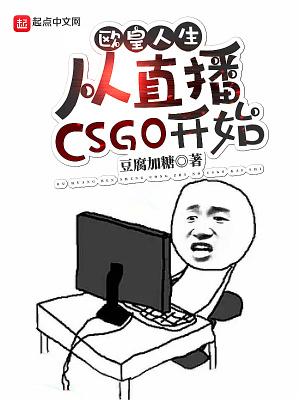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雪深春尚浅最新章节更新内容 > 第97章(第1页)
第97章(第1页)
“婚书是假的,因为当初那公子提供给她的籍契是假的,是伙同府城的官爷捏造的。”
“伪造政府文书,流刑之罪。”
“刚才说了,那曾公子家业巨大,这些事对他来说,根本是小事一桩。”
“竟是这样,”
少甯蹙眉,“这人太坏,竟用这种手段,真是令人不齿,那朝廷命官也是,伙同贼子,欺辱孤门寡女。”
“他说是对那女子一见倾心,本想直接带回家中,奈何那女子扬言誓不做妾,他只得打消了那念头,可又实在放不下,便想先用假的婚书骗她委身于他,私心想着,女人若失身于他,再有了他的孩子,待日后他将她先哄回家中,再慢慢告知详情,许她一世荣宠,她总会妥协的。”
少甯听到这,已然心下有了定论,女子虽性子刚烈,但到底争不过朝廷之人,结局应当也不会太好。
“若我是那女子,根本不会同他回家,既然婚书是假的,那便请他写了放妻书来,大家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好过让这根刺一直扎在心里,自己带着委屈活在一方小小的院落里,了此一生。”
程之衍看了她一眼,“那女子大约是同你一样的想法,所以待那正妻寻来时,说什么也要与他分开,可那男人口上答应得好好的,却暗中强行将人掠走,一路乘船带回了家中。”
少甯愤慨:‘那她那嫡母呢?就没有敲鼓鸣冤,请官爷带人追击救人?’
“那公子家中势力实在可怕,便是连府城城官也不敢管这宗事。”
少甯一怔,“莫非,这公子竟是朝中…勋贵不成?”
实则,她想的是王室子弟,只是不敢宣之于口。
程之衍却没回答她,只道:“可天有不测风云,等他们回到家中,这才发现,他的母亲被人构陷,已在家中自尽了,而往日里看重他的父亲也态度大变,不但将他逐出了继承家主的行列,后来还让人囚禁了他。”
少甯叹息一声,“也算是他的报应。”
“是。”
“那女子呢?”
程之衍笑了笑,“失踪了,有人说是被那公子的兄弟藏了起来,成了禁脔,也有人说是被她的忠仆带走了,二人浪迹天涯,更有甚者,说她生下了一个死胎,伤心太过,年纪轻轻便神志不清,跳下了悬崖。”
少甯落下两行泪来,“那那女子的嫡母定然很是伤心,她的兄嫂呢?可曾想过为她讨个公道?”
“听说她身怀六甲时,曾有幸逃了出来,只因她丈夫家族之势实在可怕,她的兄嫂唯恐牵连自身,便将她拒之了门外。”
少甯抬起头,见他停了下来,两人说着话竟到了一座宝塔下面。
她以往来法宁寺,也见过这座宝塔,听闻是用来供游客观瞻寺景所用,只是今夜却不同。
宝塔一共六层,翘脚飞檐,古韵悠久,每层均有燃着的白笼引路,可那白笼却并非同往常一般悬挂在门前或檐下,而是做成手掌般大小,围了密密一圈,紧贴着墙根。
若要拾阶而上,那些白笼便正好排在路两侧,照亮了两人脚下的路和靴。
“上去看看。”
风声渐大,少甯裹着披风也有些冷,也想寻个避风之所,便点了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往上爬,程之衍照顾她的体力,中途三次回过身牵她,却隔着衣衫,只轻轻拉住了她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