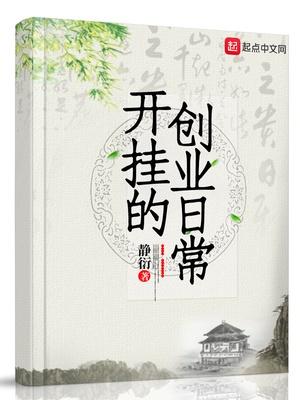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天子御刑by张听劝免费阅读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我没有!”
颜知虽有些心虚,却也急忙辩驳,并看向堂兄颜光仲,“堂兄,我真的没有!”
“有没有……县太爷会给你公道!”
颜光仲红着眼眶道,“我爹一辈子没得罪过什么人,除了你,还有谁能如此恨他!我打听了邻居,我爹失踪那几日,你便摔了腿,接连几日没有回家!哪有这样巧的事。你还不上两年前欠下的银子,又记恨着田产一事,便对我爹痛下杀手,是不是?”
堂兄所言句句在理,如果不是知道凶手是谁,恐怕连颜知自己也找不到比自己更为可疑的人。
知道在这多说无益,颜知很快冷静了下来,想到这几日他都在书院不曾下山,且很少独处,应该有许多人可以为他作证,他心里安定不少,便宽慰母亲道:“娘,不必担心。身正不怕影子斜,孩儿定不会遭人污蔑,蒙不白之冤。”
“知儿……!”
眼见衙役们欲强行将儿子带走,林氏死死拉着儿子的衣袖。
颜知不作无谓反抗,比起自身他更担心母亲,于是又转向颜光仲道:“堂兄,你疑我,我不怪你,只劳烦你帮我将母亲安全送回家中。”
“……好。颜知,你若真没有做,为兄改日定然登门致歉,给你和婶婶磕三个响头!”
颜光仲说完,便走到林氏身边,将她拉开,“婶婶,我送你回去。”
“我不要你送!”
向来柔柔弱弱的林氏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了五大三粗的颜光仲,流着泪追着衙役们去了,“知儿!”
颜知已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唯一的盼望,如何能眼睁睁看着衙役将他带走?
林氏原本就体弱,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情绪起伏,她哭泣着一路跟随,不一会儿身子便软了下去,还好那颜光仲在旁搀了一把,才不至于跌下山去。
百口莫辩
颜知被衙役们押送到县衙,推搡进公堂,双膝着地跌在了地上。
抬眼望去,高坐堂上的是个胖知县,而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伯母周氏,正哭着喊着要青天大老爷为她们一家做主。
胖知县拍了拍惊堂木,让公堂安静了些,道:“堂下之人可是颜知?”
“草民正是。”
那位知县手里拿着一张状纸,说话间仍时不时的低头看几眼:“颜知,堂下颜周氏状告你为田产纠纷杀害亲伯父,还将尸体大卸八块,弃尸于田地,你可有话辩解?”
颜知冷静道:“请大人明查,加害伯父一事纯粹子虚乌有,草民这几日都待在山上的青麓书院,不曾下山,大人若是不信……”
“即便你待在书院,难道有人时时刻刻盯紧了你?”
周氏声泪俱下地打断了他,“我夫君失踪了一天一夜,第二日才被找到尸首,你若是趁着旁人熟睡,夜里行凶,谁又会知道?”
他虽没有杀伯父,但伯父的死多少也与他有关,出于心虚与愧疚,颜知并不去看身边的伯母,只是继续向公堂之上的知县陈述:“大人,若是如此,那谁都可能犯案。况且,草民只是一个书生,以草民的体格,如何能制服得了伯父?”
“你伯父自小疼你,如何会提防?或许你假意接近,趁其不备,便将他害了,是也不是?”
颜知忍无可忍,转向周氏,“伯母口口声声诬告侄儿杀害伯父,可有什么凭据?”
周氏被他的眼神吓退了几分,这才看向堂上知县哭喊:“大人,您不要听他狡辩!我夫君极少与人结怨,唯有数年前分家,得罪过二弟一家。如今他竟遭人如此毒手,尸身也被毁,哪里是寻常人干得出来的。纵观全县,也只有他们一家能如此记恨我夫君了!”
胡知县捻了捻胡子,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道:“周氏说的在理啊,本县一向民风淳朴,若不是有仇怨,即便是杀人,又怎会要将尸身损毁成那般田地?”
“知县大人,伯父与草民确有过田产纠纷。可那已是四年前的事,当初家父过世,草民年纪不过十二岁……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伯父出了什么事,哪怕是十年二十年后,便也都要算在草民头上吗?若是如此,伯父欺我母子软弱,草民却要余生为他焚香祝祷,祈求平安了。试问,世上哪有这样的公理?”
“颜知,听说你读过几年书,果然能言善辩。那本官问你……”
胡知县道,“听说你在青麓书院打杂,以往每日都下山回家,为何你伯父遇害前后几天,一次家都未回?”
“……”
颜知沉默了一会儿,道,“草民在下山的路上跌了一跤,这才寄宿在书院几日。书院里的学生,杂役,帮厨,都可以为草民佐证。”
见颜知愣怔了一下,胡知县愈发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厉声追问:“我看你是事先在准备作案,事后又设法销毁罪证,试图逃脱罪责吧!”
说着,他将状纸往桌上一撇,腾出来的手竟已经径直朝着签筒去了。
“颜知,你还不速速从实招来,是想吃些苦头吗?”
颜知心一沉。
看来自己这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颜知若真是青麓书院的学生,胡知县或许还会忌惮着几分,可他虽然在书院听学,名义上却不过是书院里一个打杂跑腿的,知县又怎会将他放在眼里。
“拖下去,杖二十!”
令签落地,颜知被衙役们拖出堂外。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往日无论如何嘴硬的犯人,几板子下去没有一个不是满口告饶的。
可留在公堂的众人只听见十几下闷响,却听不见一声哀嚎。
众人不由心想:这小子难道是铁打的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