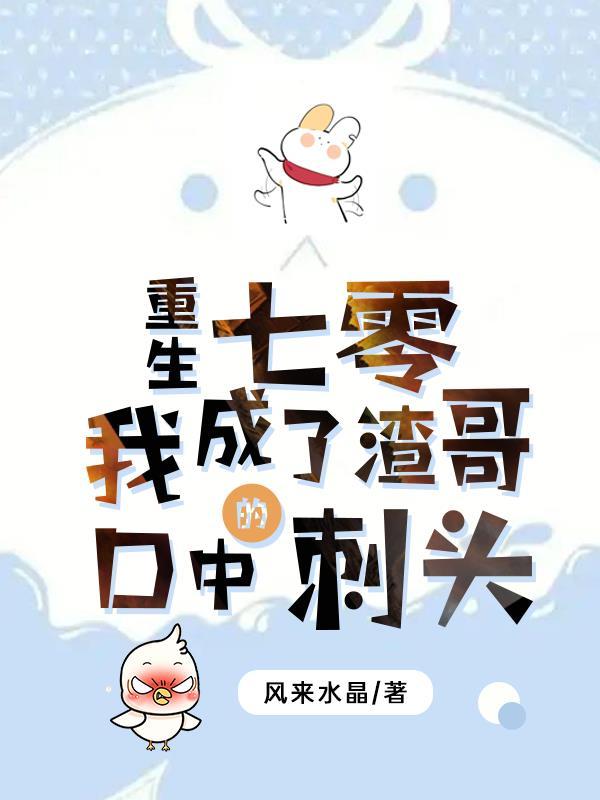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嫁给白切黑夫君以后视频免费观看 > 第三十章 酸(第1页)
第三十章 酸(第1页)
四目相对,秦葶于何呈奕一双墨黑色的眸孔中瞧见自己的身影。
他手上加了一份力,自后揽着她的腰朝前送了一分,二人身形相近,几乎贴在一起。
许是昨夜同榻而眠让他心生杂乱,今日一整日他都觉着自己的心难以入静,总似长了草,简单来说,他就想给秦葶找些麻烦。
怀里的人不知何呈奕又了什么疯,因为每次他要疯之前,都会这样先掐一番。
“朕要大婚了。”
对视良久,他自喉间挤出这个句话。
“奴婢知道。”
脸颊在他手上,脸蛋上的肉被挤在一起,连张嘴都显得费力些。
“曾几何时,朕与你在旁人眼里也算夫妻,不是吗?”
此事对秦葶来说近在眼前又似猴年马月,但她想,即便有过,与她有牵扯的人也是阿剩,并非是何呈奕。
她仅是凡尘中一粒沙,哪里敢碰瓷这般贵人。
生怕说错了什么惹他不悦,又怕他记恨从前的事将她杀之后快,秦葶在他手底下拼了命似的摇头,“陛下,那个不作数的,根本不作数的。”
“不作数吗?”
他的脸又凑近一分,“是你不想作数,还是不敢?”
他脑中有些凌乱的想,若是此刻,秦葶在他面前流眼泪,说分开的这段时间很想念他,说想留在他身边,那他便可以网开一面将她带在身边,只要她不僭越,想要的都可以给。
因此他逼迫或是诱导,不过是想要自她口中听到自己想听的言辞罢了。
只是这次,秦葶又让他失望了,秦葶的眼中不光没有泪,甚至连从前对阿剩的关心也寻不到了。
如若一只受惊的小兽,在自己面前小心翼翼。
“从前的事陛下也是迫不得已,奴婢自是不敢也不想,奴婢深知自己的身份,还请陛下放心。”
秦葶在何呈奕眼底忙着辨别,丝毫不敢沾染从前。
她越是这样,何呈奕便是越气。
好似,秦葶从来不知他想要什么。
他恨秦葶的不开窍,恨秦葶的蠢笨,于是决定更进一步,他干脆直言道:“随朕入宫。”
听到入宫两个字,秦葶脑子“嗡”
地一声,自是不愿,不光不愿,她恨不得离的他越远越好。
即便不情愿也不能表现太过,她谨慎说道:“陛下不是允了奴婢去花房吗?”
这便是很巧妙的拒绝。
何呈奕听的出来,而后他愤恨的将秦葶放开,又闹起脾气,“出去,今天晚上不必你值夜,最好别让朕见着你这张脸。”
如今何呈奕的天似六月的脸,说变就变,方才还似艳阳高照,这会儿又白日飞雪,让人料想不通,秦葶福身下去,利落离开。
徒留何呈奕在殿中怄气怄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