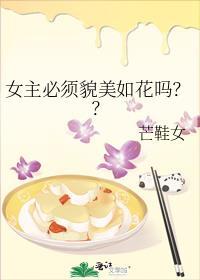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姝色难逃娄华姝 > 第三十一章 莲华野鬼(第1页)
第三十一章 莲华野鬼(第1页)
戚韫一边低声和薛鸣佩解释,一边拿着刻刀在牌子上划下了“戚韬”
的名姓,一笔一划,分外珍重。
薛鸣佩还是第一次从他眼底,看到这样深切的怀念哀伤之色。
“表哥,大表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戚韬十年前就走了,薛鸣佩没和这一位打过交道,连他长什么样都不清楚。
目送着僧人把长生牌挂了上去,戚韫道:“他?他就是个——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愚昧不堪的死心眼。”
“……”
薛鸣佩张了张嘴,发出迷惑的“啊”
。
之前看大夫人和二公子的模样,她已经脑补出了一个,风姿出尘白月光,家族楷模的大公子形象,还等着戚韫和她历数对方上到朝堂,下到府中的光辉战绩呢。
结果光听到戚韫把大哥骂了一顿。
“很奇怪?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
戚韫望着她的表情,不知道被哪里逗乐了,眉眼舒展开,“他要是个足够上进,让祖父满意的,也轮不到我这个次子担大梁。”
他坐在了树下,仰面望着层层树影,余辉碎光落了满身,仿佛衣襟上原就该有的点缀。
“怎么个无法无天,和我说说呗?”
“大哥年长我八岁,但从小就不爱读书,祖父拿着戒尺,天天把他拎去书房,亲自教养也没有用。后来皇帝有旨,让他进了宫里的崇文馆,和皇室子孙一起读书。他倒好,学问没有长进,反而和那些王孙们打成了一片,吃酒跑马,和国公府的祖宗们舞刀弄枪,玩得不亦乐乎。”
“等到他十二岁的时候,竟然还放言,以后不想进中枢,想从军投戎,去北疆做将军。”
薛鸣佩抱着膝盖,眨了眨眼:“那也很好啊。”
做大将军,在边疆守卫大好河山,这不是很有志气吗?
戚韫望着她懵懂天真的神色,语气无奈:“鸣佩,你真得不明白吗?大哥是六族的嫡长孙,人世间的芸芸百姓谁都能去边疆做将军,他却不能。”
他拿起地上一根短枝,在地上简单地画了几道线,寥寥数笔,大梁四方舆图的大致轮廓,便在他指尖隐隐浮现。
梁朝最为显赫的势力,是“三公六族”
,三个国公府掌管三方边军,驻守北、东、西的边境,六大世家根植朝堂吏治。一文治,一武功,互相忌惮。
戚韬再怎么满腔热血,皇帝也不会让他如愿。即便戚氏硬要插手,让他从军,他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谁都不敢冒那个险。
“……祖父拗不过他的狗脾气,干脆放手,让他自己去闯,在外面碰了个头破血流,自然就懂了。又见我资质尚可,转来栽培我。”
说到这里,戚韫把树枝一扔,没好气道:“就是因为他这个兄长被养歪了,给了祖父好大一个警示,轮到教我的时候,那叫一个严厉。他没半点自觉,还好意思天天烦我,要我给他的功课帮忙,糊弄过去。
你说说,有这么当大哥的吗?”
薛鸣佩听得津津有味,道:“表哥嘴上说得不客气,但我听你的语气,明明和他关系很好。”
也很怀念那个时候。
就像她,嘴上十分嫌弃郑子衿,一有什么事情就去娘那里哭诉告状,可是他离开溧州去黔西后,自己何尝不是天天惦记着他呢?
提到自己大哥闯过的祸,戚韫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原本她一直觉得这个人很远,哪怕挨着自己站在身后,也还是遥不可及,像是隔着云雾看不清楚,甚至不像个真人。可是这一刻的戚韫,却生动而真实,不再是那个人人敬畏的二公子,也不是大理寺的玉面阎王,只是戚韫。
戚韫没再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