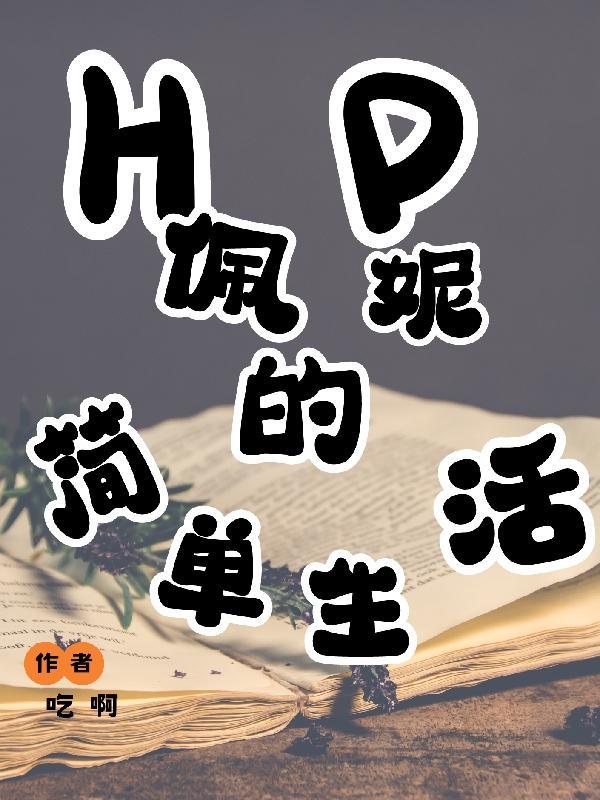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玉带生歌艺术特色 > 第67章(第1页)
第67章(第1页)
我将她的帕子捏住,缠在手指上,从她手里凑了过来,绕了又绕,揉了又揉。
“若说帝师,但凡能有真胆识的都可为帝师,今年科举的单子里,我就相中了好几个人,但是……自然还是谢卿你教的多。”
谢灵仙看着我,眨巴两下眼睛。
又摇头道:“我不信,陛下少时没有老师?”
我脑袋里闪过几个人影,便说:“我忘了,那就不作数。”
谢灵仙又歪头指着我,轻轻晃动了两下手指,“你呀你呀,若是那些先生女师知道了,定要悔起来,偏生教了你这么个忘性大的。”
封都封完了,赏也赏过了,我记不记得,重要吗,定然是不重要的。
明明是要逗她玩的,怎得如此不解风情?我要去捉住她的指尖,又被她错身躲了过去。玩闹一番,就要回太极宫了,我便垫脚折了枝玉兰递给谢灵仙。
她捧着画枝,道:“今年宫中草木长得格外好,想来今年会有喜事吧。”
自然是有喜事的。
六尚已经在赶制高悬王妃的命妇朝制。
不过几日,高宣王定亲的事传的沸沸扬扬,但世人关注的重点不是在高宣王,而是他的王妃——这位女子既不是出身于谢家这般的高门,也不是张家这样近几十年才崭露头角的仕宦之家。
而是近乎于无人知晓的东方氏。
李素似乎是知道我会宣召他询问这件事似的,流言蜚语还没传到我跟前的时候,他就主动来见我。
殿外飘着淅淅沥沥的雨丝。
我按兵不动,且看李素怎么圆话。
他先是借此讲起山野风光,再提起了他们师徒二人在山间的生活。
据李素说,他们在隐居的仙山中,萧牧河他总是窝在山里哪个角落靠着躺着,盘腿勾肩打瞌睡,完全没有王公贵族的架子,就算下山历练,也像是个富贵公子家的少爷一样。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但有意思的是,反观身为萧牧河师父的他可比自己唯一的徒弟要有精神头多了,整天在山头上跑上跑下,和村民们在山间地头干农活。
萧氏一向对宗室手段狠厉,萧牧河平平安安活这么些年,也不无缘由。
终于,他提起了东方氏。
是萧牧河游历西南时,与南朝旧地交界处遇到的姑娘,父母都是当地的教书先生,家世清白。
祖上的东方阙是前朝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后被皇帝忌惮削去官职,贬谪到临近南疆的边界之地,百年前同谢家还有过一段姻亲,后来家中没落,逐渐隐居,不再过问朝野。这倒是和徐昆玉交给我的话并不不同。
李素说:“我是看着他俩长大的,这姑娘性子上和重风相似,文静的很,心思也通透,陛下您会喜欢的。”
我只是笑了笑,没再问下去。
我应不应,对萧牧河来说或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