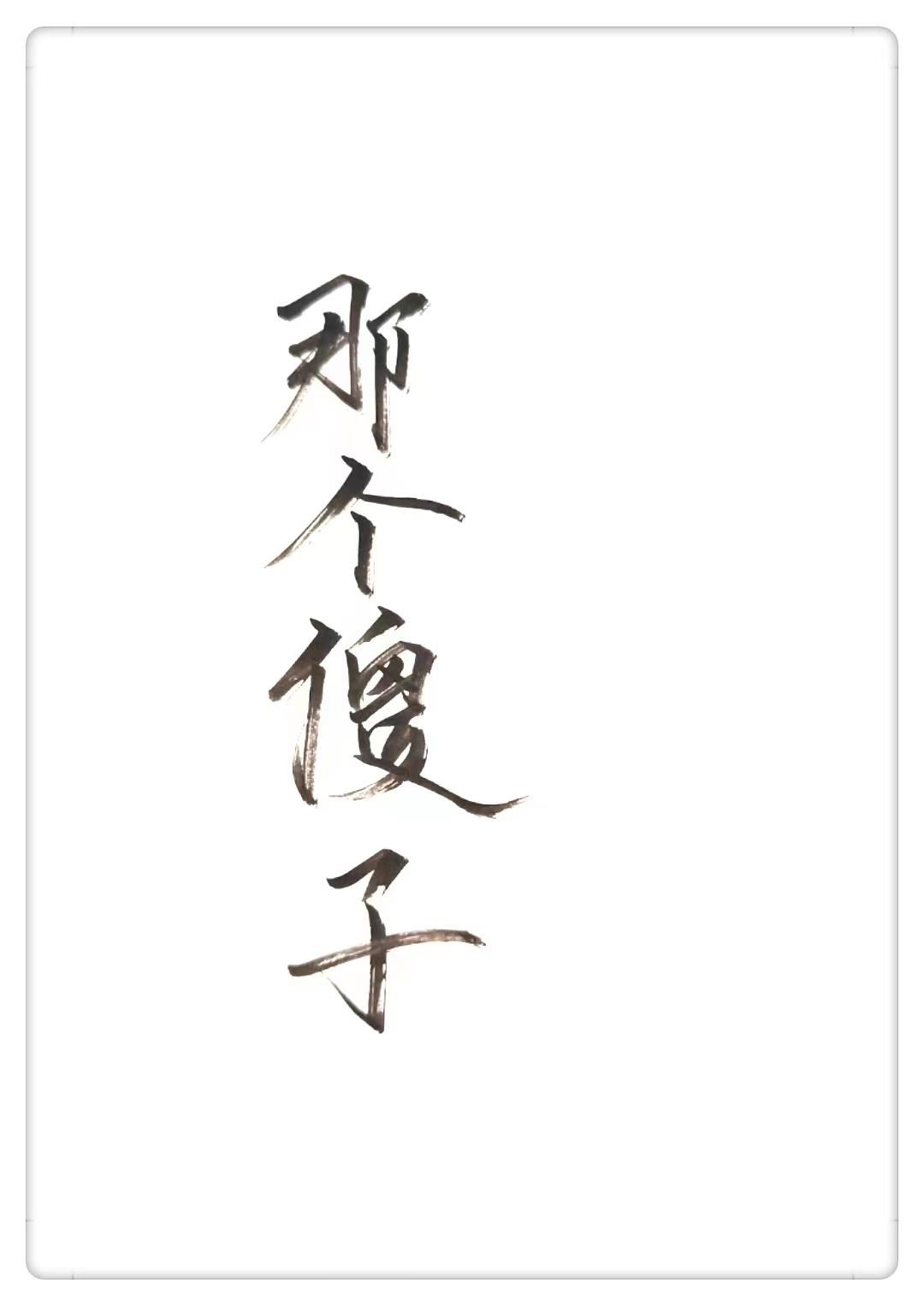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染指流连什么意思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谢砚背着她,穿过灯海,穿过人群,一边赏灯,一边往宜春台去。
姜云婵手中的帕子从脸颊划到了他高挺的鼻梁上。
说完,便起身梳洗去了。
谢晋如今只能寄希望于这些传闻是真的了。
夜幕已临,玄武街华灯初上,融融如海。
“因为,你没得选。”
谢砚掀起眼眸,威压逼人。
六条凤尾逶迤,华光倾洒,如云似雾。
谢晋悠然仰头,沐着阳光,“二弟九曲玲珑心,猜得出为什么吗?”
谢砚的棋布得够早的!
“兄长,值得。”
谢砚不以为意拍了拍谢晋的肩膀,与他再无旁话,起身掸去衣摆上的灰尘,这就要离开。
姜云婵因为缺氧,喘息连连,手软得推不动他高大的身躯。
不听话是要受罪的。
如今才知家书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实际上他在与南境总兵暗通款曲!
谢砚暗嘲,踱步离开了牢房,往玄武街去。
“发什么呆?”
姜云婵一阵痉挛,猛地睁开眼,恰见一只不安分的手穿过腰肢抚弄她。
姜云婵突然想起谢砚午间交代过她不要洗去衣裙上的脏污。
谢晋哪有什么拒绝的余地,他仰靠在墙壁上,望着那巴掌大的天窗。
她得与谢砚更亲密些,把这位公主给诈出来。
姜云婵没想到谢砚要去的竟是刑部大牢。
“闹得太狠,我怕自己明日动不了。”
姜云婵断断续续解释着。
哪里好看了?
这是谢晋第一个孩子,也会是唯一一点血脉。
姜云婵并没什么兴致与他争论这些小事,恹恹摇头,“我不碍事了,世子等我一盏茶的功夫,别耽误了正事。”
不像午间那般剧烈,可却似慢性毒药一点点吞噬着姜云婵的空气,剥夺着她的理智,让她难以挣脱。
谢砚也是这样温声安抚,说会保护她,不再让她做噩梦。
似一条小蛇游移过肌肤,姜云婵立刻寒毛倒竖。
谢砚眸色转瞬清明过来,将姜云婵湿润的发丝捋到耳后,微扬眉梢,“那明日回来再继续?”
但这也的确是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
她一顺从,他也就更温柔些,端来方才打的井水,蹲在她膝前帮她擦拭了脸颊,“妹妹今日辛苦了几遭,你先睡,我去点些凝神静气的香,檀香好吗?”
谢晋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憋得胸腔起伏,快要炸了一般,“我要面圣!我要参你养兵!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电流直往血液里窜。
姜云婵滞了须臾,帮他把鼻尖的汗也擦干净了。
偏生这样泣音黏黏软软,说出来的情话才更动人。
她在左,他在右,两个人莫名其妙就过上了寻常夫妻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