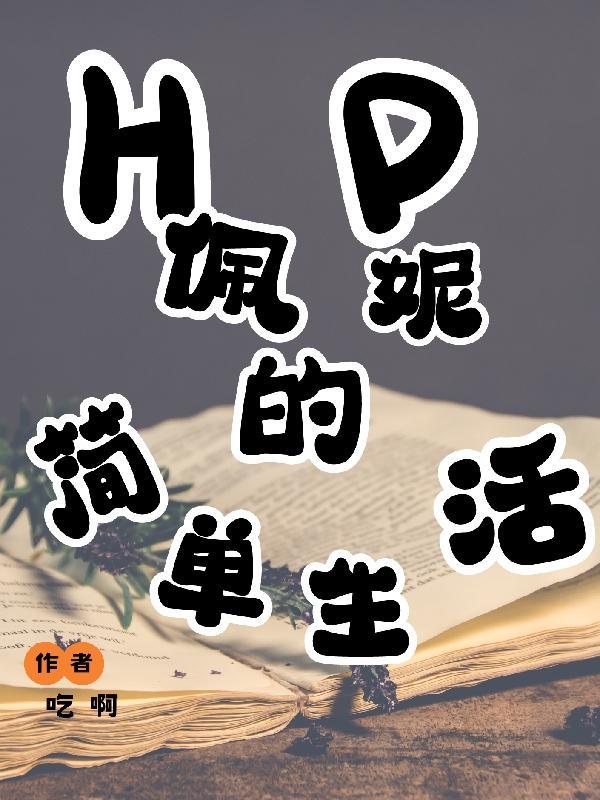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渣攻不肯离 > 第16頁(第1页)
第16頁(第1页)
杜少恆長得人高馬大,入學不久就進了校籃球隊,走起路來步子邁得大,鍾渝身體不舒服,但他又不說,硬是咬牙忍著一路跟到了校醫院。
「喲,39度3。」校醫甩了甩水銀體溫計,「輸點液吧。」
「先開藥吧。」鍾渝說。
校醫見他衣著樸素,以為他是怕花錢,好心勸道:「最近流感高發,輸液好得快些,你是學生醫保可以報銷。」
鍾渝搖了搖頭,堅持道:「開藥就行,麻煩醫生了。」
杜少恆在一邊看不過去了,忍不住道:「醫生說輸液就輸液唄,你難道還怕打針啊?」
鍾渝抬眸,淡淡地看了杜少恆一眼。
他不是怕打針,只是不喜歡待在醫院,討厭白色的牆和藍色的窗簾,以及空氣里刺鼻的消毒水味——因為這些是母親住院的那段時間裡,留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東西,對他來說總是象徵著痛苦與死亡。
不得不說,他那雙眼睛是真漂亮,此刻因著發燒,眼眶紅彤彤的,泛著潤澤水汽。就那麼平靜地看過來,不帶任何情緒,但偏偏會說話似的,讓你沒法對他說重話。
杜少恆投降了,「行吧,開藥就開藥。」
醫生被他逗樂了,問:「你們是同班同學嗎?」
「我是他室友。」杜少恆抱臂坐在一旁,嘟囔:「個不省心的。」
咋就這麼倔?也不知道他今天是怎麼發著高燒考試的,那麼大個人了還照顧不好自己,杜少恆操碎了一顆老媽子心。
醫生開好了處方,鍾渝繳費取了藥,被杜少恆親自押送回寢室。
白色退燒藥片混著溫水服下,鍾渝躺在床上,沉默了好一會兒後,忽然喚道:「杜少恆。」
杜少恆剛打開電腦,準備上遊戲,聽見自己的名字,不明所以地抬起頭來:「嘎哈呢?」
「謝謝。」鍾渝由衷地說。
杜少恆被他認真的語氣弄得一怔。
對於這個室友,他的第一印象是漂亮,不是女相的那種漂亮,也不僅僅局限於五官的精緻,還有一種獨特的、疏離的氣質。
——就是他明明在對你笑,人也溫和客氣,但讓人覺得難以真正地靠近。
於是第二印象是他安靜,安靜到近乎孤僻。
報導那天,杜少恆是和爸媽一起來的,大一生正好是剛成年的年紀,清澈愚蠢好奇心重,家長難免會不放心孩子出遠門,因此大多都會陪著孩子報導。
他帶著爸媽去宿舍,剛打開門就看到了在整理書桌的鐘渝。
室友初次見面,杜少恆是個自來熟社牛,熱情地上前打招呼:「誒?你好啊!咱以後就是室友了!」
對方手上拿著本書,聞言抬起頭來,溫溫和和地回了句「你好」。
他生得好看,又和自己孩子同齡,就容易招阿姨輩的人喜歡,比如杜少恆他媽——程娟女士是個話癆,邊忙活邊和這小同學嘮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