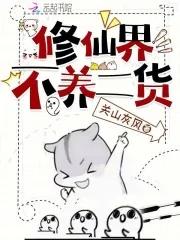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阴阳灵气概论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她如何疯魔都拦不住那辆冰冷的推车。
就如,父亲当年费尽口舌也拦不住她。
他一生都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终究那把炽烈的火将他化为乌有。
从人变成一捧细渣子,灰呛呛一片,扒拉扒拉,其中有5颗漆黑的指甲盖大小的颗粒。
见到那东西的瞬间,认识他并信任他的火化工人老付,“扑通”
跪下,老泪纵横胡乱嚷道:“老哥哥千古哇,这是去西天极乐做佛爷了!”
刘喜英第一个冲上去将尚有余温的骨珠全部握在手里,贴在脸皮上,泪水打湿表面,恨不得立刻与之融为一体。
她哭着笑了。
失去焦点的眼睛四下乱瞟,看不清围上来的人都是谁,举起那几颗珠子,抽噎着说:“看,你们看……这是我爸的舍利子……我爸成佛啦!他再也不会死了!他去过好日子了……爸,我错了……爸,我错了!”
她早就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个没留住的孩子开始,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
他的出轨不是现在才有的,很早就有了。虽在同省,生长在地大物博的黑土地上,想回趟娘家都不容易,嫁过去以后才知道千山万水之隔是什么意思。
他对她还是那么好,可那份好不止属于她,也属于那些和他打情骂俏的女人。
在那边生活多年,她交下不少体己的朋友邻居。挚爱的丈夫却是这些人嘴里的谈资——
他跟隔壁邻居家的女人眉来眼去;又和楼下麻将馆认识的女人传出闲话;陪他出去参加同事聚餐,她都能听见饭桌上奚落他不正经的言论……说什么的都有,她只当那是玩笑不曾当真。
她以为只要这样催眠自己,就能和他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可那些话积攒多了还是成了心病。
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闷闷不乐跟她说,亲眼看到于叔叔在街口和一个漂亮阿姨手拉手。
她慌了,呵斥儿子,指责他胡说八道。一着急,羊水破了,肚子里的那个急吼吼地提早一个半月降生。儿子被吓得六神无主,哭着跑出去叫来邻居婶子,送她去的医院。
东北流传过一句邪门话:七活八不活。说是七个月大的胎儿早产能活,但八个月大的怎么都活不成。
她信了。于是更加害怕,拖着产后疲惫的身躯,舍弃脸面致电父亲,要他赶过来,为自己的女儿祈福续命。
父亲却说:“这孩子跟你无缘,喜英啊,不要强求了……爸现在有个事实在走不开,我让你妈去——”
她“啪”
地挂了电话,连多余的话都不想再跟他说,后来很久都不愿搭理他。
没出一年,先天性心肺功能不全的女儿没了。刘喜英抱着她没了生息的身体差点哭瞎眼睛。
母亲和姐姐匆匆赶来陪伴她。没能看到父亲的身影,痛失爱女的刘喜英见到亲人的瞬间破口大骂:“都给我滚!不用你们管我!我不认他这个爹,他咒死我老弟又咒死我姑娘,他早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母亲上前狠狠给了她一嘴巴,扯住另外两个女儿扭身就走。
这份倔强一脉相承,痛苦和离别都改变不了一家人根儿上带的脾气。
就那么执拗很久很久,父亲将死之时,刘喜英才低下高昂的头颅,回到惦念的故乡。
走到他面前,什么都没说,只是握住他颤抖伸来的手。
千头万绪哽在心头,父女俩双双不言语。
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准把菜里的花椒都挑出来,没让她尝过那个咬一口就犯恶心的作料;她也会在他解完手走出厕所,递给他一张滚水泡过的毛巾。
因为医院的卫生间水龙头只出冷水,他不习惯,她就把毛巾泡透了,攥在手里耐心等他。
从始至终,刘喜英没亲口跟父亲道过歉。临了,还是他拉着她气若游丝地说:“老儿子……爸对不住你。我不是个好爹啊……我混吶我——”
看他哭了,她强忍着悲伤牵起嘴角,边给他擦泪边安慰他,“胡说,你咋不是好爹呢?你是最好的爹了……爸,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尿床那次吗,我妈睁开眼就揍我一顿,你就拦着还骂她,嘿嘿,还记得不……”
病久了,一阵清醒一阵糊涂,听什么都嗯啊答应。
刘喜英慢慢说着旧事,慢慢帮他擦洗身子。
说着说着,爸爸睡着了。
睡着睡着,爸爸就走了。
她失声痛哭,搂着他的脖子凄声喊他。
声声入耳,深深刻在刘钰脑海里,每每想起都会湿了眼眶。
两个老同学听完她老姑和她爷爷的故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勋可擤完大鼻涕,气愤捶桌:“你老姑父太不是物了!他家在哪,你跟我说,我领人揍他去!”
“嗐,轮不到你,据说我奶把他脸都掐青了。”
刘钰抽出两张纸分别递给他们,看准了梁欢红肿的眼睛,郑重道,“今天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陪我哭的。梁欢,你既然来找我,我希望你能相信我……雷春龙真不是什么值得托付的人,你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你的好姻缘在后头呢,再等两年吧。”
“我才不等呢。”
梁欢揉着眼睛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我现在也不是真的对他有多深的感情,就是挺喜欢他的,你就别管我了,让我再好好痛快几天。玩玩嘛,你放心,我听你的,指定不带深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