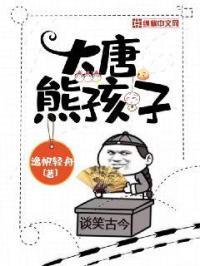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一树桃花的意思 > 第1章(第2页)
第1章(第2页)
他当时就蒙了,急忙到船运公司定了船票。正好过去的同学润名也要回国,两人就结伴同行了。他对自己的事情自然也就略知一二。
“我一人在船舱里想了很多……”
他突然说,眼睛看着远处隐约可见的陆地。
“想什么?”
润名很高兴他愿意与自己聊天。
溥铦伸手摸了摸自己冰凉的鼻尖:“人的生命真脆弱,说走就走了--”
“那是,咽气不咽气就那么一下,过去了就过去了。你应当节哀才是。”
他料定溥铦的额娘已经死了。
“我一个下午都在想她,想她为我做过什么事。可是想了很久,关于她的记忆几乎是空白的。我自己都奇怪,明明心里是酸的,可就哭不出来--”
他眺望远处的目光落在了同伴身上:“你说怪不怪?”
“有什么怪的?咱们这些人,永远都觉得乳娘比亲娘来得亲。老实说,我要不是带了我家老太爷和老太太的照片,早就把他们给忘了……”
他所说的“这些人”
是指满族的亲贵。
“你老婆呢?也忘了?”
溥铦心不在焉地问。
润名冷笑几声,说不出话来。
“你跟她说了没有?”
溥铦瞥了一眼远处与人高声谈笑的女子--正是刚才怏怏而去的白种女人。
润名也转过头,似陶醉道:“她很可爱。”
“女人只对忠诚的男人可爱。”
溥铦的语气很冷:“回到北京后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老婆离婚?”
“我不知道,”
润名沉吟了一声:“船到桥头自然直,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看你啊--玩火自焚。”
溥铦双臂纠缠地挡在胸前,头靠后,下了这个结论。
“这话怎么说?”
他明知故问。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没听过这话?”
溥铦由于疲劳,懒得将训话的腔调变得圆润。润名听得刺耳,愤然起身:“我要回去了,你也别在这呆了。”
溥铦摇头,便不再多说话了。
回家
两天后,船靠岸,是在香港。溥铦和润名一同下船,却不与他同行。原因就是他讨厌那个外国女人。虽然说她长得还不错,但人太矫情。更何况那两位在谈恋爱,自己夹在中间当电灯泡明显是多余,他们觉得晃眼不说,自己也觉得不自在,还不如独来独往,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