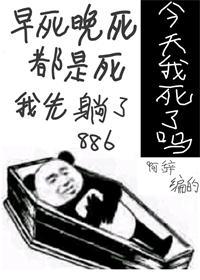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女扮男装升官指南慕峙 > 第28章(第1页)
第28章(第1页)
老者仿佛听不出话中的嘲讽,只一个劲儿地埋头作揖:“孩子的病耽搁不得,税银我马上去筹,求官爷开开恩,再宽限几日……”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办不成差事回去也没法儿交差呀。”
话虽如此,税吏面上却未见几多急迫,而是对着老者继续出言讽刺:“你本来就干不动活儿了,还带着这么个拖油瓶,一大把年纪了还天天忙里忙外的,没攒下一个铜板不说,反倒欠了一屁股债,棺材本儿都赔进去了吧?”
“你说说,你不辛苦谁辛苦?”
“就是,依我看呐,什么时候这小拖油瓶病死了,你才能过几天自在日子哟……”
眼见他们越说越过分,江抒怀听不下去了,刚要上前,手腕忽然被人攥住:“别过去。”
安蕴秀蹙眉道:“此行只是昭告世人我们已经为宋首辅所用而已,末了将所探之事理作卷宗呈上便罢。我们并无官爵在身,不宜贸然出手。”
她虽怜悯这对祖孙被税款所压生活艰难,却也知道税吏是按律行事,若想相帮,事后赠些银两即可。可若贸然出手,且不说自己与江抒怀恐难全身而退,这对祖孙是否会被秋后算账也未可知。
毕竟盯着改革税制的人多了,自己与江抒怀近日来的行动,想来也是被有心之人看在眼里的。
“你怎能说出这种话?”
江抒怀却是很气愤,连带着对她方才敷衍态度的怒气一并迸发:“宋首辅如此信任你,派你来调查此事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吗?眼下众生苦难皆上映在你我眼前,你竟是要视而不见吗?”
“我不是要置此事于不理,而是……”
“甲儿!”
一声极悲极痛的呼喊响起,正是来自于老者。
正在争执的二人心中猛地一沉,再次看向那边时,只见原本满脸惶恐地躲在爷爷身后的小孩,已经了无生气地躺在地上了,后脑正正撞在一块石头上。
“呃……”
一名税吏悻悻地收回手,辩解道,“我就轻轻碰了一下,想把他拉出来看看而已,谁知道这小孩儿这么弱不禁风。”
“咳,我说老李头你也别太伤心,拖油瓶没了,你以后的日子也能过得好些不是?”
“……”
这一下来得猝不及防,安蕴秀头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看到江抒怀要冲出去,便唯有不能让他出去这一个念头。
“别过去!”
种种利弊得失的计算仿佛骤然失去光彩,一条活生生的性命足以成为午夜梦回时萦绕不散的扣问。安蕴秀咬紧牙关,只死死地抓住最后一丝清明,告诉江抒怀:“先离开这儿!”
他们二人规规矩矩地相识、相处,没有一见如故互诉衷肠的佳话,却又彼此欣赏,端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未有过今日这般怒目而视不肯相让的局面,也从未想过,会如亡命之徒一般奔过野草矮坡,推搡着要握紧或挣脱腕间的那只手。
待停下来时,面前一派天广地阔,野草闲花随风摇曳,像是踏青游玩的好地方,那片混乱不堪的血腥之地已被甩在身后很远。
安蕴秀放开了江抒怀:“这里出了人命,无论是田庄地主还是税吏定会有所动作,多半是遮掩此事。命案的目击者可不是什么好身份,我们不该出面。”
几句话的功夫,她仿佛已经从方才的慌乱中恢复,开口声音十分冷静:“事已至此,我们应当想想后续该怎么办,而不是让自己也身陷泥潭。”
“如此铁石心肠之人,哈,实是不多见。”
江抒怀神色难看,似乎忍无可忍:“可你若当真如此狠得下心,到手的仇敌把柄,又为何要放他一条生路?”
“……”
“他”
是谁,二人皆心知肚明。
安蕴秀没料到他忽然提起徐开荣之事,心中仿佛被刺了一下。沉默许久,她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那江公子你呢,你科举入仕,是为了兼济天下吗?”
江抒怀身形骤然僵硬,思及自己入仕的初衷,这句问话犹如当头一棒。
“安会元。”
他声音艰涩道,“你真是个天生的诛心弄权者。”
黎民之忧
葳蕤绿树掩映了江抒怀愤然离去的背影,浅飞的雀蝶扇动翅膀,送来一阵酒气。几个学子模样的人出现在不远处,笑嘻嘻地要请安会元移步喝两杯。
安蕴秀木然地瞥了一眼,竟还从中看到了几张熟悉面孔。看来此地确实是个踏青游玩的好去处,只不过同年仕子们对于早早便崭露头角的自己和江抒怀显然不是很服气,方才二人不欢而散的场面,怕是要成为一则流传许久的笑话。
她理了理情绪,躬身谢绝了这番“好意”
,随即转身离开。
天远地阔,却不知去处在何。安蕴秀走了一阵便茫然地停下脚步,心中郁气不散,恍惚间碰到腰间缀着的钱袋里还有几块碎银,才回神一般要去看看那对祖孙。
此刻,佃农尽数散去,大槐树下只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抱着了无生气的孙儿在痛哭。几个税吏站在一旁交头接耳,似乎在讨论该怎么处理这事。
哭声呕哑,不忍卒听,似乎还伴随着江抒怀尚未散去的质问。安蕴秀行至不远处停下,垂眸看向被自己攥到变形的钱袋,恍惚间觉得烫手至极。
我不像安蕴林,我只知道,若是不往上爬,徐开荣家里一个小小管事就能要了我的命。此来京城,最开始是为了自保,后来又想着复仇,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也可以解黎民之忧。
及至此时,方始悲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