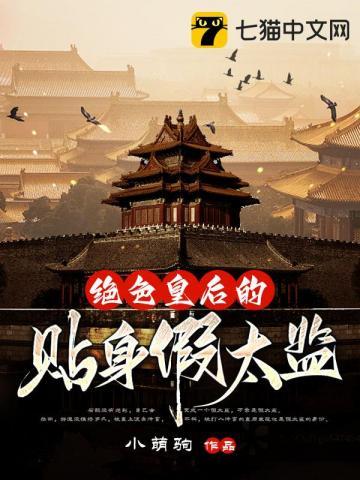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认错太子为夫君后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是昨日那位夫人。
她眼波温柔如水,有着姑母的从容平和,也有着晏书珩的温煦。
纵使阿姒再冷静,但在深陷敌营时遇到一人对她温柔抚慰,不免会生出信赖,她抓住妇人的手,像抓住救命稻草:“我,他……他死了……()”
哐当——?()_[(()”
刀剑落地,元洄从帐内走出,余光不经意看了眼阿姒,继而转向母亲:“回母亲话,此人已杀。”
“好。”
妇人温和颔首,她虽柔弱,但面对血光面不改色,察觉阿姒双手发抖,还柔声宽慰:“别怕,背主之人,死不足惜。可怜你被吓着了,下回若有这种事,不必亲自动手。”
随即她告诉阿姒,自己姓赵本是魏兴人士。听她也是大周人,阿姒多了些亲近,她感激地谢过赵氏。
一旁冷眼旁观的慕容凛见她们说得差不多了,冷声插话:“人本王已给你,你该兑现承诺了。”
父亲舍命护下的东西,即便已然无用,又岂能交给外敌?阿姒纠结良久,看上去像是在性命与忠孝之间徘徊,但最终妥协于生死:“……父亲出事前,曾托人给我带话,让我记得回阳翟城外的翟山庙为亡母点灯。因从前我常与他去那给亡母点灯,我并不清楚此话是否暗藏玄机,但我父亲遇害是在翟山庙。没有别处比那儿更有可能。”
之所以说翟山庙,是因她一早便派了几人先行赶往那里,试图探一探那是否留下些旧时踪迹。
说不定她的人会碰上慕容凛的人,再顺藤摸瓜寻到她踪迹。
慕容凛淡淡扫她一眼,唤来一人:“你带人去阳翟探个究竟。”
阿姒对上他冷厉的眸,刻意哆嗦了下,小声道:“你们……能不能别打砸物件?那庙中供着我母亲灵位,一向鲜有人去,如今当还完好。”
慕容凛不为所动。
赵氏侧过头:“一个无父无母的可怜女郎,纵身陷敌营也不忘为父报仇,王爷亦为人父母,别做得太绝。”
阿姒看出赵氏在他面前能说得上话,很有眼力见地躲到她身后。
慕容凛扯起嘴角,似看出她的狡黠,但未再计较,利落地大步离去:“罢了,念在她手刃仇敌的胆识肖似夫人当年模样,暂且放她一马。”
阿姒暂时松口气。
她折身要回营帐,可想到这里死过人,步子便迈不开了。
赵氏细心,温声道:“我那有空余的营帐,你去那附近陪我吧。”
“多谢夫人。”
阿姒紧跟在赵氏身后走了。
元洄立在原地,若有所思地看着阿姒远去的背影,她正紧跟在他母亲身后,像只无措的雏鸟。
一年前,她也是这样小步跟在他身后,怯生生地唤他“夫君”
。
往事不可追。拂去记忆里那个温软的声音,元洄回想今日。
在与阿姒交涉前,父亲先把他叫了去:“你素来认为女子柔弱,构不成威胁。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世间女
()子如何用温柔无害的皮囊迷惑人。()”
元洄遵从父命,在帐外听着。
柔婉但冷静的女声像把剪子,过往记忆被绞得面目全非。
那个曾柔声唤他夫君,无助得失去他庇护便无法生存的女郎,在面对他父亲时展露出的冷静和睿智出乎他意料,那是与生俱来的聪慧和果敢。
或许她当初也是如此给他下套。
阿姒在他心里的印象突然变得复杂,但也更为鲜活。
她原是这样的女子。
默然拾起地上宝剑,元洄手触到她剑柄上她握过之处,不由紧了下。
父亲也有失算之时。
他不该来。
。
晚间,赵氏精神头颇好,唤阿姒陪她出去走走。
此处白日里望去乱草丛生,一到晚间流萤纷飞,如梦似幻。
阿姒借机问赵氏这是何地。
在陈留郡境内。?()_[(()”
赵氏看出她一心琢磨着如何离去,但并未戒备,笑了笑,“你和我年轻时很像,不过我那时没你聪明,被亲人几度出卖,直过了几年才想明白。我亲手杀了那人,一剑封喉,那是我的亲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