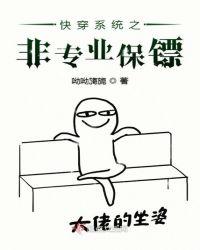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在逃公主知乎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这不是巧了吗,张渥张院副姓张,张封业也姓张。
她饶有兴味地走出存药堂,一抬头正对上一双疑惑的眼睛。
张封业出了存药堂也没走远,就在外边一棵古杏树下守株待兔呢,结果“兔子”
是等到了,就是这兔子挂着狡黠的笑,像是晃一晃便能听见她一肚子的坏水。
真是稀奇了,陈仲因那呆板无趣的人,竟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就算被撞个正着,杜宣缘也没有半分赧然,大方摆手,请对方先行一步。
这回反轮到张封业踌躇了。
虽说他在这儿杵着就是在等陈仲因,但现在这态势,好像有一点儿不对劲。
不过在杜宣缘投来询问的目光时,张封业一振袖,抬步随她走到一旁的少人小径上。
就在张封业忖度着如何开口,将主动权拨到自己手中时,便闻杜宣缘老神在在道:“承绩兄进出存药堂轻车熟路啊。”
张封业一顿,正对上她含笑的双眼。
“呵。”
他没回答,而是感慨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诚不欺我。”
“我来寻承绩兄闲庭信步,承绩兄也恰巧在堂外等候,可不是你我二人意气相投?”
杜宣缘淡然道。
张封业心说他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想逗一逗呆头雁,却反被雁啄。
他可不信什么茅塞顿开,观“陈仲因”
这小子现今的做派,他恐怕是早有预谋,先前竟能在太医院伪装数月,心思实在难测。
想到这里,张封业心念一动,问道:“你我共事数月,一向交情浅浅,如何今日能聊上几句秘事,莫非……天意如此?”
杜宣缘敛眉——张封业这话倒是与她尚未宣之于口的某些打算不谋而合,她既不否认,也没给出肯定的答复,只笑道:“纸包不住火,火中取栗,当然要做好灼伤自己的准备。”
张封业闻言开怀起来,眉眼间皆是喜意,但口中却道:“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无所事事四处闲逛,但却是个眼瞎耳聋的,见不到旁人将手伸进火堆里的热闹。”
语调平平,却带着几分怨怼。
杜宣缘更加笃定张封业知道些什么。
她顺着张封业的话道:“可这火在眼前烧起来,火舌都燎到眉毛了,又如何能一无所觉呢?”
张封业反问她:“那你在此地数月,为何装傻充愣?”
杜宣缘心说:那是因为陈仲因是真傻!要不怎么能被人当背锅工具人呢?
不过她面上仍是笑吟吟道:“若我装傻充愣,如今又怎么能与你在此闲谈呢?”
张封业果然被她的话术引导,双目一亮,道:“这么说,昨日……”
杜宣缘高深莫测地轻轻颔首,压低声音道:“我手中已有确凿证据,只是孤证难立,才领命多有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