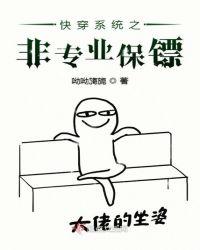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在逃女团什么意思 > 第54章(第1页)
第54章(第1页)
皮猴们见到“饲养员”
也个顶个的兴奋,再顾不上手头那些佶屈聱牙的字符,一个接一个从席位上爬起来,向杜宣缘奔来。
像一只只快乐的小狗,凑到她跟前用仰慕与期待的目光直直注视着她,面对这样的眼神,少有人能不心软下来,抚摸一下他们柔软的头发、捏一捏柔软稚嫩的耳尖。
“去问玫夏姐姐要,我把东西给她了。”
杜宣缘将手中的布包背到身后,又拍着其中一个孩子尚且单薄的肩膀,把他们全部引走。
眨眼间,这群“天大地大、吃饭最大”
的孩子们已经一窝蜂跑没影儿了。
杜宣缘是一点儿打扰到陈仲因教书育人事业的自觉都没有,寻摸了一席之地坐下,看向好似在发呆的陈仲因。
陈仲因的发呆从不是表面看上去那般呆滞,有时候杜宣缘真挺想扒开他的天灵盖看看小陈太医成日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能让他时时刻刻陷入自己的世界中。
“不好意思。”
还是杜宣缘先开口打断这让人无言的默然,“打断你的教学了。”
“无事。”
陈仲因摇头,“他们早便开始晃神,不过碍于师长之威,不敢放肆罢了。”
杜宣缘稀奇地看向陈仲因,心道:我可一点儿都没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师长之威”
。
不过师长威不威的与她无关,她也不做人家的学生。
杜宣缘将方才藏在身后躲避那群皮猴探究的布包拿出来,递给陈仲因,在对方颇为疑惑的神情中眉眼飞扬,十分得意。
陈仲因揭开布包,只见里边整整齐齐码着三本册子。
第一本他再熟悉不过,是陈仲因从前在太医院任职时做的手札。
而后边两本,皆是太医院藏书的手抄,墨迹虽干,墨香犹存,挑选的书籍皆是院中言简意赅的精品。
看着全然陌生的笔迹,陈仲因料想这应当是杜宣缘的字迹。
只是出乎陈仲因所料的,这笔迹既没有杜宣缘本貌的秀美端庄,也没有杜宣缘灵魂的狂放不羁,但这字也不是毫无特点,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分明是出自一个能够出口成章、外貌翩翩佳人的手,却和此时此地,那一片狼藉的稚子席间露出的一页、半页字迹十分相似。
简而言之,没有任何美感,像是初学者的涂鸦,能做到横撇竖捺都清晰呈现已经是大幸了。
无论是谁,都很难从这样的抄录中专注于内容而非字迹。
陈仲因忍不住看向杜宣缘,手中还捧着翻开的抄本,其目光的含义不言而喻。
杜宣缘挑眉,双手抱肘倚靠着门沿,没好气道:“看我干嘛,我五岁就辍学了。你还能指望一个失学十几年的大龄儿童给你表演一手出色的丹青妙笔吗?”
陈仲因下意识摇头,是想要辩解,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千言万语被锁在喉咙口,到头来憋出一句:“若你有闲暇,也可来此习字。”
杜宣缘心道:刚还说自己也不是他学生呢,这家伙便上赶着来做老师了。
她笑道:“免了,跟那群小不点一块学写字,你当我是留了十五年级吗?我忙得很,这字你能看懂就行,没必要练。”
陈仲因听不懂“留级”
是什么意思,但也能听出杜宣缘言辞间推拒的意思,他抿着唇低头抱紧手中的抄录,轻声道:“太医院中的藏书有许多孤本、私密,轻易不让抄录出来,多谢你……只是以后还是别带给我了。”
他说说停停,似乎是觉得自己的话生硬到有“不识好人心”
之嫌,可又的确担心杜宣缘受此牵连……他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如何纠正自己的词不达意。
好在杜宣缘并不在意这种细节,她挥挥手,道:“我有我的法子,绝不会被人抓住,你尽管放心。”
话说完,她还双眼微眯,故作警惕地盯着陈仲因道:“除非你拿着证据告发我。”
陈仲因这人一向容易把别人的玩笑话当真,立马言辞凿凿地保证绝不会做这种无耻之事,又把杜宣缘逗乐了,只是她笑得不夸张,陈仲因以为是她相信自己的保证。
杜宣缘临走的时候又扫了眼有些乱糟糟的小厅,在陈仲因收拾碰落在地的纸墨笔砚时,忽然开口道:“到底是在同一屋檐下,相处久了总会生出些感情,即便早已告诫过自己,但我还是担心会养出白眼狼来。”
陈仲因动作一顿,某一刻有些分不清杜宣缘说得究竟是谁。
又闻杜宣缘道:“不过也是我自找的,怕麻烦关起来就是了,只要掌握在手上就好了,何必好吃好喝的供着,再寄托以情绪呢?”
陈仲因越听越觉得是在说自己。
失策、失策
陈仲因手上收拾的动作越发迟钝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又或许是哪里都没做好,盖因身在此山中而一无所觉——只觉脸上臊得慌。
杜宣缘最后一锤定音,道:“过几日史源盈要被押送至黄州,我带他的弟弟妹妹们去城外送一送他,陈先生可要安排好教学时间呀。”
她说完以后,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只有陈仲因听到这话,终于从僵硬的状态下挣脱出来,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而他背后轻薄的衣物已经被汗水浸湿。
。
自从上次的交锋被张封业打断后,这二人都不愿再落下风,谁也没去主动找对方继续这个话题。
陈三似是自觉已经看透杜宣缘的行径,也多出几分耐性等待,而杜宣缘就更无所谓了,她十五年都等得来,还差这一时半会儿的耐心吗?
于是这几日,二人愣是一面都没有撞见过,从一个“莫名其妙就会擦肩而过”
的极端到了另一个“共事太医院却好像阴阳相隔”
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