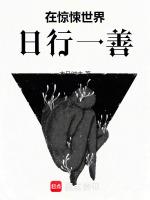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玫瑰雨是什么意思 > 第69章(第2页)
第69章(第2页)
“她不在?”
“不在。”
“你指给我位置,我进去放她课桌。”
见女孩如此生分,章萤其实怀疑过是不是那天进她家结果被谌降截道,谌降是不是跟她说了什么,但转念一想凭他们的关系和谌降的性格应该不至于,于是颇为受伤地扮可怜,“你连这点小事都要防我吗?”
课铃快打响了,宋惊晚没有时间再继续耗,将冻疮膏交给她,“谢谢,麻烦了。”
章萤冲女生笑笑。
小小冻疮膏自己无须折腾心思,章萤走到崔无恙的课桌边,不过并不打算告诉她是谁送的。崔无恙正垂着脑袋,貌似在盯着手掌中的某样东西出神,连自己在她身旁都浑然不知,章萤看清了,是那对玫瑰耳钉。
崔无恙分外珍惜它,凝视的目光也分外柔和。
很不对劲。
直觉告诉章萤,很不对劲。
只是个物件而已,哪怕做工再精美再喜欢也不该流露出这样的表情。
要么,她不是惦记物件,而是惦记耳钉意指的人。起码在章萤的印象里,崔无恙就像玉面罗剎,是没有软肋的,她待人接物总是冰冷,不像情感丰沛的人。
为此,章萤多留了个心眼。
送完冻疮膏,宋惊晚回班里上自习课,手早已冻得没知觉。
今天坐在讲台的值日班长是许冕,见女孩稍稍迟到并未苛责扣分,宋惊晚蹑手蹑脚地走向座位,然后拿起笔写作业。
从门缝灌进来的冷风不息,宋惊晚写一会儿便停笔,搓搓手掌生热,如此循环往复,十分钟过去仅写完了蓝本的一面,效率极低。她握笔的姿势僵硬,因此写出来的字体不够顺滑,每一撇一捺像被打骨折似的,宋惊晚越瞧越不顺眼,强迫症犯了,写得更慢。
谌降快写完了,她还在老地方乌龟爬,他不清楚原由,习惯性嘴贱:“很难么?求我我教教你。”
她瞪他,同时无意识地朝掌心哈气,感觉筋骨活络点便继续写。谌降敛了笑,问:“你很冷?”
又写难看了一个字,宋惊晚悲愤地托腮生闷气,没理。
“手。”
他言简意赅。
“干嘛?你给我暖啊。”
宋惊晚撇嘴。
“不会又说我吃你豆腐?”
谌降有的时候喜欢干脆些、强硬些的直接用行动说话,径自抓住女孩的右手,又是十指相扣的姿势,宋惊晚吓得眼圆一圈,强行把他和自己的手都摁到了桌子底下。
她挣他,但谌降握紧了就是不放,这个精神病。
“你疯了?被别人看见怎么办。”
男生慢条斯理:“谁?许冕么。”
宋惊晚不懂,为什么其他同桌牵个小手都和和美美的,轮到自己和谌降,照旧跟战争一样,互相之间暗暗较劲。她没能挣过他,认了命,选择安安分分地被他紧攥着,听见少年轻叹:“好凉。”
无法否认的是,被他扣住的右手正在渐渐攀温,男生的热量犹如永不枯竭的太阳,源源不断地给自己传递温度,慢慢疏通了僵硬的血管。指腹以及掌心的血色愈发红润,手恢复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