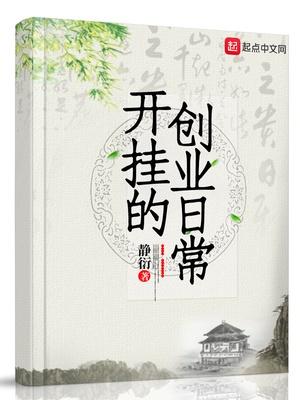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圈养番外要问问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我不敢去看他,闭上了眼,拳头握的很紧,牙关紧咬着,眼睛是要充血的红,我好想理智的清醒下来,告诉他不要再说了,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我用力喘着气,等到终于恢复理智的时候,才睁开眼睛。
与此同时,何以初放在一边的手机响了一下,屏幕随之亮起。
我条件反射的看了一眼。
只这一眼,就把我刚才辛苦建造的所有心理防线给掀退,理智退去,刚才脑子里的自我克制都消失不见了,胸腔里呼呼燃烧着什么,时刻等待着我失控。
【闫航】:小初小初!给你看看我的腹肌嘿嘿嘿,就问你馋不馋!是不是今晚做梦都要梦到我了!
何以初扫了一眼屏幕,他伸手去拿手机,我大脑里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却彻底断了。
我有些粗鲁的握住他的手腕,制止他的动作,眼睛直直看着他,声音很沉很冷,“腹肌?馋不馋?做梦?”
我死死盯着何以初,不肯放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说出的话都带上了几分咬牙切齿,“何以初,他为什么要给你发这种信息?你跟他很熟吗?他不是刚转学过来吗?他都在跟你聊些”
“哥哥。”
何以初眨了眨眼,他挣脱了一下我的手,没挣动,也不恼,只微微靠近,“今天我跟闫航说话,哥哥是不是吃醋了?”
我盯着他,喉结上下滚动,在这一刻,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的小朋友,远比我自己要勇敢。
“我”
我偏开眼,握着他手腕的手松了力气,自暴自弃的抬头,手放在头顶胡乱抓了抓,很艰难的扯出来一个笑。
“对不起。”
我说,“哥哥只是担心”
话没说完,生生被打断。
何以初似乎是再也不想听我说这些话,他整个人用力往前一扑,跪在我跟前,双手使劲搂住我的脖子,随之撞上来的是他的嘴唇,青涩的,莽撞的,不管不顾的。
他撞上来的时候很用力,鼻子跟我的鼻子贴在一起,泛起了很酸很涩的疼。
嘴唇贴上来还不够,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唇瓣相碰就会满足的小朋友。
他急切地动作,牙齿胡乱蹭咬,冒冒失失的伸出舌尖,在我唇瓣四周舔舐,他张着嘴,小口喘着气,舌尖不知羞的往我的唇缝里钻。
我睁着眼睛,呼吸依旧平静,心脏却乱的早已溃不成军。
我看着近在眼前的何以初的睫毛,微微垂着,胡乱颤抖。
投影仪的光打在他脸上,时而暗时而亮起,暧昧朦胧,让人控制不住的眩晕。
耳边是他小声又不加克制的喘息,他整个人用力往我身上贴,贴的严丝合缝,密不可分。
你有没有听到过心动的声音。
那是克制,是失控,是溃不成军,是防不胜防,是下意识的回吻,是一万次的视线相交。
是何以初眼睛里的星星,是我扣在他后脑勺越来越重的力道。
郁闷
当多巴胺分泌过多的时候,交感神经激烈碰撞,肾上腺素飙升,大脑也就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甚至连思考的功能都跟着消失了。
伴随着最后一根弦的彻底断裂,我几乎是无意识的控住了何以初的大脑,更用力地将他压向自己,明明两具身体已经贴的快要窒息,却仍觉得不够,还想再近,还要更近。
何以初像一只软软的猫,他塌着腰趴在我身上,被我控着头,往上仰起脖子,纤长的颈线很漂亮,混合着喘息的口水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淫靡一片。
明明脸蛋都被憋红了,呼气声都开始不均匀,他仍固执的抓着我的衣服,很配合的张开嘴,努力承受着我越来越紧迫的进攻。
我可以掌控他的情绪,还可以轻易掌控住他的身体。
这个认知让我神经都跟着亢奋,指尖微微颤抖,于是吻的越来越凶,掐着他腰的手很用力,指印都要印上去。
电影播放到报幕阶段,没了光,只不断闪过几行文字,夜色开始翻滚,渐渐吞噬整个房间。
周遭不断升温,何以初的身体滚烫,他被我放到床上,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看向我时的眼睛湿润,嘴巴也湿,亮晶晶的,微张着小口轻轻喘息。
我眼神暗了暗,这一刻,什么该死的伦理道德都被我抛到脑后,一切都是空白的,听觉、视觉、触觉无限放大,却也只聚焦到了一个他。
我欺身而上,感受着他柔软的舌尖小心试探,摸到他皮肤上细细密密的汗,听着他猫咪一样的低唤。
这个吻缠绵了很久,断断续续的没有尽头。
那个沉默的夜里,我跟何以初没人再说话,只是躺在床上,断断续续的,安静跟对方接吻。
他很容易就累,被我亲一会儿就有些受不住,张着嘴小口喘气。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把他放开,手掌慢慢陷进他的头发里,细密的磨,漆黑的眼睛一直看着他,怎么都看不够。
等他歇的差不多了,我就再次毫无征兆的亲下去,亲他的嘴唇,很轻很慢的咬,亲他的下巴跟可爱的喉结。
最后他软软的在我怀里睡去,手还抓着我的衣服,发出来很轻的呼吸。
我擦掉他嘴角的水渍,小心查看了他的腿,目光沉沉落在他脸上,描摹着他五官的每一寸。
凌晨一点,我毫无困意,甚至很想去楼下跑两圈。
落在何以初脸上的目光沉沉的,暗涌着情绪翻滚,我强压下心头的种种苦涩。在这一刻,在这个夜里,我只想做一个失了桅杆的船,甘愿沉海,甘愿飘荡,甘愿丢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