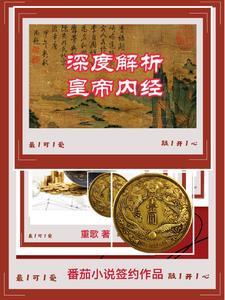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二度为后王爷 > 第218节(第1页)
第218节(第1页)
只听着喜儿冷笑一声:“但凡主子在紫薇堂一日,我一日便不离开这里。若是女王西去了,我便跟着主子一道戴孝,横竖都是几年的孝期,也不好嫁娶。等过了几年,谁又能知晓那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时候谁能笑到最后都还难说。况且兔子被逼急了还咬人呢,我若是真被逼的无法了,只多剃度出家做个尼姑也好。若是尼姑都做不成,那便是只有一死了。主子常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这自然是鸿毛之轻,可是又如何,总比好过守活寡空闺要强。”
方衿一听,禁不住笑了一声:“喜儿,你可是越发的没谱了,说的都是没脸没皮的话了,连这样的话都能说出口了,可见你确实是一点嫁郡王的心思都没有。”
喜儿道:“事已至此,我还有的选择么,没脸没皮又如何,总比得事事被牵制,最后无可奈何空落泪要强。你不信,不如咱们走着瞧,看这最后到底是太妃犟的过主子,还是主子强的过太妃。太妃今儿个不是说了么,叫我问问家中娘亲,我娘亲如今不过是在九泉之下了,我若是去问她,自也会拉个垫背。”
“可怜你父母都不在,这话是有些不在理了。倒是不如我,娘亲与爹爹都在。”
方衿若有所思道。
喜儿听了觉着心下怪异,倒是从来未听闻方衿提起自个父母来,如今这话,倒像是爹娘都在南疆的意思了,这么一想,就觉着有些不对劲,只是讪讪地应了一声:“父母不俱在又如何,我不愿意,她便杀了我,不然就休想叫我屈服。”
两人正说着话呢,却见外头来了一个嬷嬷,自称是浚郡王的奶娘,便是秦嬷嬷了。她从前也是先王的奶妈,身份自然尊贵,就连女王见了也得礼让三分。
那秦嬷嬷以来,见了喜儿便道;“可叫我好找,原来姑娘在屋子里头,你便跟我来,咱们坐一处好好说说话可好?”
喜儿假意不知道:“见过嬷嬷,可不巧呢,我们主子吩咐了要做绣活,可没空说闲话,不如改明儿您得空了再来。”
秦嬷嬷笑笑:“什么绣活可忙成这样,不如我去与你们主子说,这些绣活太辛苦,你也不必做了。倒还是咱们说说体己的话要紧。”
喜儿道:“有什么要紧的话呢,也不用专门挑地方了,嬷嬷不如就在这里说,喜儿洗耳恭听。”
秦嬷嬷摇头道:“可不是好话,可只得与你一个人说了才行。横竖也是天大的喜事呢。”
喜儿一听,即刻起了身,笑道:“嬷嬷,我不过是个没念过书的乡下的丫头,说话粗野,您也莫见怪。这好事,能有什么好事,见喜长痘那也是喜事,路边捡钱,那也是好事。可是倘若说做人小妾是好事,那是闻所未闻了。您说这一过去进的就是偏门,成日抑郁寡欢的,有什么可值得做的。我便是真从了那浚郡王,只怕是您日子也不好过。我这可是有失心疯的,保不准哪一日发了病,磨了刀子砍了谁,可就真说不好了。”
喜儿边说,边从屋里头拿了几件小玩意来,狠命往地上连连摔着,可把秦嬷嬷急的直跳脚。那方衿见喜儿如今是撒泼的模样,自然吓得连连往后躲。
秦嬷嬷面色发白,气的横眉倒竖,说道:“你愿不愿意的,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倒也用不着说三道四地骂着,可真当是乡下来的丫头没教养,亏你们主子教的好。倘若今儿个是旁人告诉我,我倒是不信了,你们主子可是知礼数的主,想来身边的丫头也不会差。如今看来倒是脾性差极了,但凡给你三分薄面,你可就蹬鼻子上脸去了。亏得我今儿个是亲耳听到了,若是传到了旁人耳里,还不知晓闹成什么样呢。”
秦嬷嬷边说,边赌气离开了。喜儿气的还要骂,方衿此时方才敢上前,略劝了几句,便由着她去了。这一夜漫长,喜儿自然没睡着。
茱萸早早就命人送了早点过来,说是知晓她没什么精神,便送些粥食来,也算是补补气力。才吃了两口,又听见外头有人唤,说是女王找她。喜儿只得梳洗一番,方才跟着内侍一路到了玉壶殿。
彼时,茱萸、女王、浚郡王、太妃、太后、秦嬷嬷等人,再加这宫里头有头有脸的几个人人皆已在位置上坐着。喜儿一见,知晓今儿个是进了龙门阵了,倒也放下心来,但是面对面,摊开了说,她倒不怕。就怕不说出来,背后使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