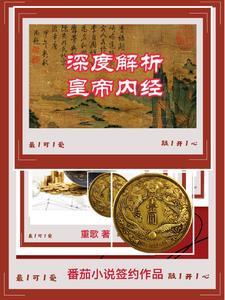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权臣的在逃白月光 第208章 > 第三十三章(第1页)
第三十三章(第1页)
四月的天气,一日比一日明媚,今日尤甚,阳光暖融融的,湛蓝的天空竟是一丝白云都未见着。
长安街头依旧车水马龙,只是各大茶馆都隐隐有些躁动。
一辆马车急行,在员外府门前才堪堪停下,身着华贵的男子踩着人凳落地,进府时的步伐多少有些气急败坏。
秦羽在家中已经躺了快半个月。
但俗话说得好,伤筋动骨一百天,他断了两根肋骨,半个月了,还夜夜疼得睡不着。
秦执进来的时候,他正望着头上的帷幔骂娘。
他娘的王宥,他这身伤不是他的手笔,秦羽两個字他倒过来写!
“你还有脸骂?”
秦执怒气冲冲地进来,“当初怎么与你交代的?叫你去和王宥攀交,不是叫你与他结仇!你倒好,你自己便罢了,如今他妈把爷也带上了!”
秦羽忍痛扬起半个脑袋:“大哥,确定了吗?真是国公府世子?”
“今日滴血认亲,想来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若非已经有十成把握,国公府怎可能容它传得满城皆知!今个滴血认亲就连陛下都去了国公府,这事儿还能有纰漏?!”
秦执握着扇子的手恨不得要将那纸扇给折断了。
这世间还真是无奇不有。
怎就那么巧,寻了十几年的人,居然近在眼前。
幸亏那日在云听楼秦羽只是揍了他的仆人一顿,事后他也还回来了,那日在琼林宴,他与他也只是言语冲突,否则将来与国公府的梁子是结定了!
“大哥,他不是官都还没授吗?我们怕什么。”
秦羽嘴硬地嘟囔。
秦执一扇子扔过去:“蠢货!他要进了国公府,还在乎那点官位吗?你以为这半个月过去了还未授官是为什么?那是陛下在等!他若只是个寒门出来的状元,充其量也就一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但他若是国公府的世子,怎可能只封个从六品小官!”
秦羽被他一扇子磕得呲牙咧嘴,他就是个浑的,这么些年哪些人能惹哪些人不能惹他是清楚的,但为什么能惹为什么不能惹,他就不想那么多了。
大抵就是官比他叔父做得大呗。
“那等我养好伤给他赔礼道个歉去?”
秦羽是叫他勇,他绝对没有顾忌,叫他怂,他也能怂得心甘情愿那种。
秦执背着手在屋内慢踱几步,心绪平静下来,缓声道;“倒也不急。”
倘若此前秦羽能与王宥交好,当然是好事一桩,但他尚是一介布衣时便孤傲清高,不欲攀附他们,这回了国公府,岂不是更要高高在上?
何须拿热脸去贴冷屁股,讨不到好不说,凭地丢人。
“且先看他进了国公府,到底能有何造化。”
秦执捡回自己的扇子,嘴角浮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国公府世子又如何?长公主的嫡子又如何?到底姓裴不姓楚。
这氏族圈子,可不是那些穷酸家族里,左右只有三俩歪瓜裂枣那么好打。
-
温凝这些日子过得都不太得劲。
菱兰眼瞅着她又过回去了,成了前阵子那场大病之后的模样。醒着的时候步子不停,踱过来踱过去,睡觉的时候呢,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好的模样。
她都在考虑是否要喊郎中来,再给她开些安神的方子了。
“开什么开,我心里安定得很。”
温凝仰面就给自己灌了一杯凉茶,“你可别忘了,咱们前阵子刚赚了五千两银子呢!这么好的事儿,心里有什么可焦躁的?!”
菱兰咂咂嘴。
这话里的火药味,恨不得要将那凉茶喷热了,还说自己心中安定……
她也不与温凝多说,转身出了香缇院。
她家姑娘不爽快的原因,她能猜到一二。一是这半月来被禁足,只能在自己的院子,充其量再去东厢窜窜门,难免憋得慌;二呢,前阵子捉婿失败,虽然姑娘未说过什么,外头也很快有别的新鲜事,让姑娘不至于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话,但总归是会失意的罢。
菱兰觉着,这心病,还需心药医。
她去了东厢,温阑的院子,请温阑去讲些外头有趣的事儿,姑娘心情总能好一些。
温阑正好下值,心里有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情绪无处可讲,菱兰过去将话一说,他便净手,去了香缇院。
温凝正百无聊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