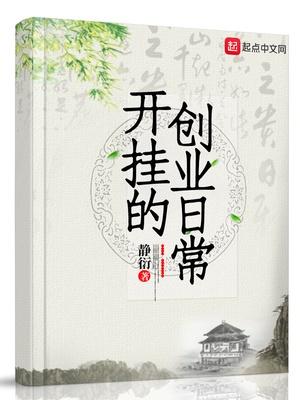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今天沙雕学长弯了吗by芝芝猫猫 > 第89頁(第1页)
第89頁(第1页)
給段野洲打電話的人貌似在生很大的氣,呂儒律不用調低電影的聲音都能把他的話聽得一清二楚:「……一整個寒假一個電話都沒有,大年三十也不知道打電話問候父母,等我老了還能指望你?」
「隨你指不指望。」段野洲懶懶散散地說,「我這邊信號不好,掛了。」
呂儒律看著段野洲踩著積雪朝他走來。以往每次和家裡打完電話,段野洲的心情或多或少會變差。但這一次,聽他輕鬆愉快的腳步聲,就知道他的心情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呂儒律開玩笑地問:「這麼冷淡,萬一你爸不肯把你寫進遺囑里怎麼辦?」
段野洲從他手裡搶走烤串,咬下最後一片五花肉:「不寫就不寫吧,以後沒錢了我就去LV修車行打工。」
呂儒律哼笑一聲:「難怪要費盡心機地討好我爸我媽,原來是在和未來老闆老闆娘套近乎。」
段野洲十分震驚:「怎麼辦……居然被律哥識破了。」
夜深後,三人滅了篝火回到帳篷。呂爸把大的氣墊床讓給兩個小的睡,自己則在簡易的行軍床上湊活了一夜。
次日,呂爸照例起了個大早,背上漁具冰釣去了。兩個小的即使是在戶外也堅持著冬天賴床的優良傳統,直到呂儒律收到一條校內通知,驚覺自己忘了件大事,垂死病中驚坐起,把枕在他小腹上玩手機的學弟都掀了下去。
今天,是教務系統開放選課的日子,也是決定他們下學期快樂與否的日子。而他們學校的教務系統是遭萬人唾棄的垃圾和卡頓,選課時稍有不慎就可能斷送一個大學生一學期的幸福。
呂儒律看著自己打視頻都一卡一卡的信號,陷入空前絕後大危機。
和他視頻的是瀾書小情侶。謝瀾之享受著拉滿的網,告誡他:「別的課程怎麼選都行,但《現代密碼學》最好不要選唐教授的課。」
呂儒律一個激靈:「唐教授很變態嗎?」
謝瀾之輕描淡寫地說:「還好。他只是每堂課必點名,遲到必扣平時分,有事沒事就抽人隨堂測驗而已。」
秦書笑容滿面地補充:「聽說隨堂測驗如果表現不好,也會被扣平時分的哦。」
呂儒律捂住胸口:「……救。」
對唐教授這樣敬業的老師,學生們一般都是敬而遠之,只有在搶不到其他教授課的情況下才會去選他的課。
呂儒律一層層套上衣服,高舉手機衝出帳篷。
雪地里,旋轉,跳躍,他睜著眼;
陽光下,白雪,冬日,他不停歇。
他拼盡全力燃燒著生命去尋找,去靠近,去捕捉那珍稀的信號。
然而,現實有的時候真的很殘忍。他在冰天雪地里苦苦追尋,累得狂呼白霧,手機上的信號依舊停留在要人命的兩格。
段野洲懶洋洋地站在一旁看沙雕學長一通折騰,打了個哈欠:「有什麼我可以幫到律哥的嗎?」
呂儒律氣喘吁吁地撐著膝蓋,無法接受地瞪著腳下的一片雪地。
——結束了嗎?這就是他的極限了?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不!!!
呂儒律倏地看向學弟:「段野洲,你能讓我騎一下嗎?」
段野洲:「?」
呂爸的冰釣之旅收穫頗豐。他拎著兩條大魚回到營地,想著中午給兒子烤魚吃,卻因眼前的一幕愣在了原地。
只見白茫茫的雪原上,他那個2o歲,身高181的兒子正要……往他學弟肩膀上坐。
段野洲蹲在呂儒律面前,呂儒律兩條腿跨過他的肩膀,段野洲一個起身,把他輕輕鬆鬆地扛了起來。
陽光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在地上,仿佛雪都要被他們的美好青春融化了。
這個姿勢呂爸並不陌生,兒子小時候也是這樣坐在他肩膀上。現在長大了,不騎老爸的肩膀,怎麼改換學弟騎了?
呂儒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上回段野洲背他高得多的多。低頭向下看的時候,他都有點恐高了。
他擔心自己摔下去,只敢用一隻手拿手機,正猶豫要不要用另一隻手抓穩段野洲的頭髮,段野洲就抬起手,牽住了他,還帶著他的手晃了晃:「信號會好點嗎?」
呂儒律盯著手機,失望地「嘖」了一聲,懊惱道:「還是不行啊。」
「那怎麼辦。」段野洲說,「要不你踩我頭上吧。」
想起昨天說了好幾次冷笑話段野洲都沒有理他,呂儒律這次也沒有理段野洲的冷幽默。他坐在段野洲肩膀上環顧四周,看到不遠處有棵大樹,連忙舉起和段野洲握在一起的手朝那個方向指去:「去那邊,段野洲,送我上樹!」
段野洲無奈道:「律哥,你不用這麼拼吧。就算你被迫選了唐教授的課,你最後肯定也能得高分的。」
呂儒律怒道:「你懂個屁。96分和95。8分它能一樣嗎?!」
段野洲:「……呵,學霸。」
爬樹這項技能呂儒律小時候頗為精通,現已生疏許久,好在有段野洲在他像夏蟬一樣抱在樹幹上動不了的時候托著他的屁股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順利到達了更大的高度。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手機上的信號終於增加了一格。
呂儒律站在一根結實的樹枝上,一動不敢動,生怕稍微轉個身信號就要減弱。
離選課系統開放還有最後三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