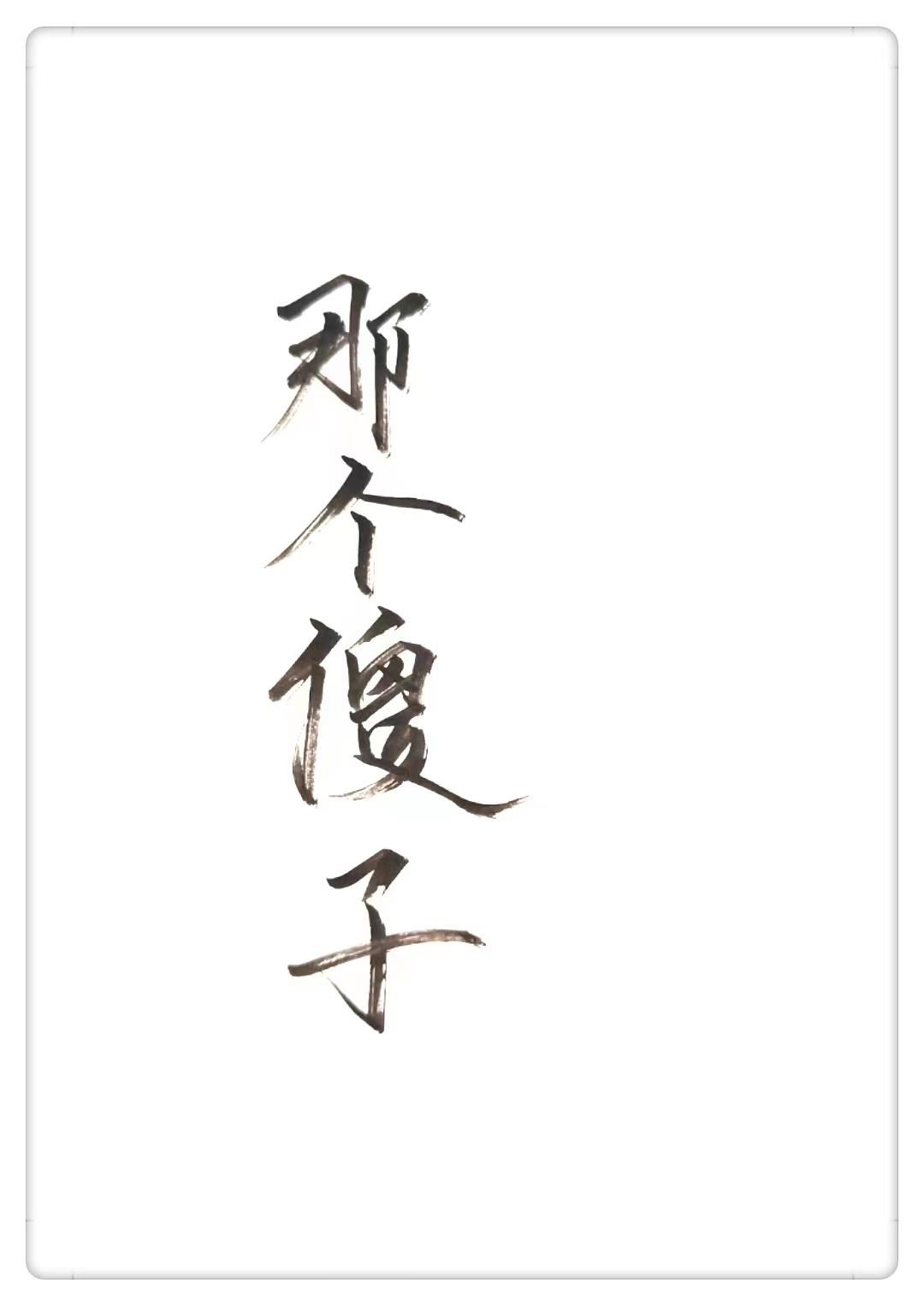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万人嫌死后成了白月光免费 > 第86章(第1页)
第86章(第1页)
温然现在也并不急着走,他甚至微微笑起来,欣赏起傅尧不知所措的丑态,用上了自己觉得刻薄的话,“那个你最讨厌的温然。”
傅尧觉得面前的人可能是生病了,不然怎么会说出这样胡编乱造的话来,他罕见地磕巴起来,一开始拼命拽住温然的手却奇异地渐松,他勉强笑了一下,“怎么了?是不是之前撞到脑袋了,现在还没好?”
“我讲得足够清楚,我是温然。”
他的声音一字一顿清晰明朗地渡进傅尧的耳畔。
“温然?”
傅尧五官的面容扭曲一瞬,他自言自语,看起来像是在安慰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傅尧将温然拽到客厅里一扇透明的窗前,上面能够反映出两人大致的轮廓和五官。
“你看,明明还是闻夏的脸,五官,还有声音,全都一模一样。”
傅尧难受地抓了抓领口,费劲地咽下发哽的喉咙,“这些事是温然告诉你的吧?你们什么时候见过面的?什么时候认识的?”
“是不是闻夏,你现在不也已经心知肚明了吗?”
温然冷然拂开傅尧的手掌,对着那张印照出闻夏五官的窗面,“不然你可以去问谢衍——”
“那闻夏呢?”
傅尧表情空白几秒钟后迟疑道。
温然抿唇不语。
“那闻夏··在哪里呢?”
傅尧声音缓缓降低,变得跟雪花一样轻飘飘,眼底变得晦暗看不太清,他甚至没有像往日那般,一把凶狠地用手指勒住他的头发,残忍地逼问:“闻夏呢?你把闻夏弄到哪里去了?”
他失魂落魄地往庭院跑去,显然是去找谢衍对峙,温然揉了揉被他掐得发疼的胳膊,瞧了一眼傅尧的背影后就往外走。
在走至雕花大门时,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温然看了一下屏幕,是温静冬。
“小夏,你为什么又往我的账户上转钱了呀?”
温静冬的声音很柔和,可能因为中年,本来强硬的脾气到现在略微有了收敛。
“那是温然留下来的,之前一直被别人交管着,我想,现在交给您是最合适的。”
他解释着。
可那端莫名陷入一阵突然的沉默,“我···”
温静冬想起后来因为家庭将温然撵走,心口潮水上涌般钝钝的难受,语调颤抖,却竭力强忍着,“我后来对他并不好。”
“人已死,这些也没那么重要了。”
温然保持一个姿势有些累,将拿着手机的右手换成左手,耳廓边温静冬的声音徐徐传来,温然认真听着,聊了几句后就挂断。
在快要走出大门之前,他给闻母打了一个电话,冷清的眉眼变得轻柔,“我今天就不回来了,我一个朋友喊我出去玩呢,可能会通宵一个晚上。”
闻母在电话里问:“那你晚上住哪里?”
温然嘴唇扬起的弧度宛若起了涟漪温柔的湖,“酒店,您不用担心。”
闻母没再过多探寻隐私,“那你切记注意安全,另外,祝玩得开心哦。”
温然:“好。”
温然将手机收进口袋,不疾不徐往外走着,在快踏出大门的那一刻,别墅外面挺直站立的司机早已恭候多时,“谢先生吩咐让我送您。”
温然还没来得及拒绝,司机就已经倾身将后车座的车门打开,恭敬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温然这次顺从他的好意,前脚刚踏进车内,身躯微躬,在车门即将关上的最后一刻,别墅里面传来一声破天般撕心裂肺的吼叫,随即是强忍不住,带有讽刺意味的爽朗笑声,仿佛要刺透整个蔚蓝天际。
他手一停,最终将车窗摇了上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完全隔离起来。
车汇入主干道后,温然让司机在下一个路口停下,临走之前弯身道过一句谢谢。
商圈附近的酒店还挺多,温然随便找了一家登记住了进去,他身上没有带别的东西,只有一个手机和身份证。
拿到房卡后温然乘坐电梯上去,电梯里面有一面宽大干净的镜面,镜子被里面的灯光照射到反光,但是依旧能够清楚地映照出里面的面容。
即便是相处长达半年之久,温然到现在还是觉得眼前的这张脸带着生疏。
陌生的灵魂与躯体互相碰撞之后,虽然从外表看不出来,就像黄昏跟晨曦一样,乍眼望去,两者相似到极致,一样绚丽的色彩在无垠的天际蔓延开来,可时间一长,就渐渐显露出巧妙的端倪。
温然现在也怕看到自己面前的这张脸,他害怕闻母在发现自己的性格缺点后,逼问自己:闻夏呢?
他卑劣且贪婪地占据别人的一切,并且日久起了贪恋,甚至想长久地将那一份自己从来得到过的东西牢牢攥住不放。
温然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他没有办法控制。
可他秉性还在,没办法做到拿了人家的东西不去归还,没法像闻父那样安慰自己,“夏夏在手术台的时候已经死了。”
他没办法。
房卡在感应器上发出一声“叮”
的轻响,温然将门打开,房间的装潢简约大气,处处透着精致。
他把门合上,将自己摔进宽敞柔软的丝绒被中,脸颊深深地埋在里面,仿佛要将自己憋到窒息。
温然躺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将近七点,已经隐约有黑沉下来的趋势,他从床上摸出手机,打开邮件信箱编辑了很长一段话,是发给闻熄的。可是在结尾时,发现刚写下的内容蹩脚且矫情,后来全部删除了,只留下几句,然而设置的定时发送。
他打算先去洗个澡,打开水开关,在浴缸里放满温热的水,眼睁睁地看着水位一点一点蔓延上升,白色腾腾的雾气也开始将整个浴室填满,攀附在玻璃上,有的已经凝结成水珠从玻璃上蜿蜒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