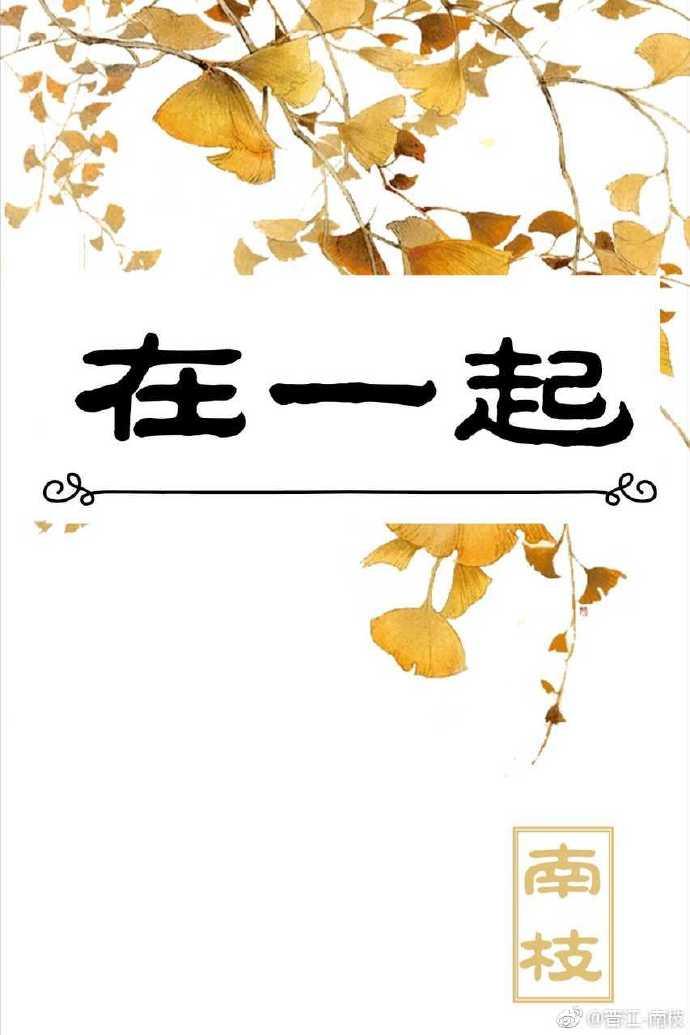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纨绔休妻记百度 > 第195章(第1页)
第195章(第1页)
他察觉,胸前的衣衫凉凉地贴在了身上,她哭的有些厉害,对他说着好。
“我对你说的话,做的事,都是真的。”
好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一样,他再也没有顾忌,再也没有心思赌气,也不知到底是病痛不支不得不依靠着她,还是故意抱着她,总之,两个人依偎着,温暖着彼此。
他的声音低弱的像个垂死之人,在做最后告别,伏在她的脑顶,概因病痛的缘故竟带出许多深沉的温柔,“你真好看,可惜,人生太短……”
罗婉的眼泪愈发叫他惹了出来,她牢牢抱着他,支撑着他的身子,对外面道:“大夫呢!快叫大夫来!”
大夫自然还是诊不出宗越中了什么毒,为着做戏只能找几处无关紧要的穴位扎一扎,放出一点血,宗越配合地稍稍缓解了痛苦的神色。
“大夫,可有性命之忧?”
鉴于方才宗越那一番出自肺腑的“临终遗言”
,罗婉对他中毒一事深信不疑。
葛大夫是宗越安排的,知道此时该说什么,“脉象看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但世子头痛欲裂,明日的考试恐怕……”
“我能去。”
宗越刻意压低声音,露出虽然微弱但势必与病痛抗争到底的倔强。
这份不屈不挠的倔强自然惹来了罗婉疼惜的目光,她握着他的手安抚道:“越郎,好好养病,我们来日方长,不急在这一次。”
宗越摇头,说什么都不答应,坚持带病考试,对葛大夫说:“不管什么办法,暂时压制住我的头痛。”
葛大夫佯作既同情又钦佩宗越的遭遇,一口应下,说着家中有祖传的镇痛丹,这就去为他拿来,又道:“不过这药只能压制一时痛楚,药效一过,痛感会千倍百倍也不一定,且是药三分毒,这药一味压制而不疏散,对身体其实弊大于利,若非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服用。”
罗婉听了,自然不同意,宗越却道:“只管拿来。”
送走葛大夫,罗婉并没立即折回昆玉院,而是去了前厅。
“我儿到底如何?”
安丰侯问。
宗越忽然重病的消息惊动了整个宗家,其余几房也都赶来探看,方才差点把昆玉院堵了,是宗越嫌吵闹,撵他们到厅堂侯消息。
罗婉将大夫的话原原本本学给众人,也说了花糕的事。
话音才落,听夏氏一声冷笑。
她看向宗季蓉,脸上没有半点为人母亲的慈爱,冷嘲热讽道:“瞧瞧,你平时多亲近你嫂嫂,出了事,还不是先怀疑你?人心隔肚皮,何况你和人家,还隔着肚皮。”
宗季蓉看夏氏一眼,没有反驳,转而看向安丰侯,直接说道:“爹爹,那花糕不是我做的,是二姐姐做的。”
接着便说了前因后果。
听罢,堂上一片死寂,众人心中都已有判断,是宗孟芙毒害宗越无疑。
“造孽!”
安丰侯重重一拳砸在桌案上,道:“去把人给我抓过来!”
“侯爷!”
夏氏哭嚷着跪在他面前,“阿芙刚出月子没几日,孩子多病,丈夫落难,整日郁郁寡欢,你还这么对她,是要杀了她吗?”
“阿芙现在还不够可怜吗?谁说她送的花糕有问题,谁说明檀的病一定是因为那花糕?”
夏氏心里很清楚,罗婉若有实打实的证据说宗越重病是花糕的缘故,恐怕早就来求公道了,不会如此温和。
“侯爷,瑞王虽然落难,可阿芙是你的亲女儿啊,元郎是她的亲阿兄,她回来娘家,从没有对元郎露出过怨恨,她给元郎送花糕,一定也是真心实意的,您怎么能把她想得那么坏?”
夏氏哭诉,泣涕涟涟,惹得两个小儿子也都跪过来为宗孟芙求情。
安丰侯也生了犹豫,心底自是不信宗孟芙真能做出毒害宗越的事。
罗婉见状,说道:“父亲,我来不是要追究谁,兄妹之间一时不和,打打闹闹很正常,到底是家务事,我也没打算闹到官府。只是,越郎为病痛折磨,即便如此,他还想着明日的考试,不惜冒险服用镇痛的药,也坚决要去参加考试。我来只是想请父亲查明,二妹到底在花糕里放了什么,好让大夫对症下药。”
宗孟芙终究是瑞王妃,又刚刚诞下一子,谁也不敢动,只能请安丰侯这位父亲出马,威逼也好利诱也罢,哪怕安丰侯不追究宗孟芙的罪责,只要能问出宗越中的药毒就好。
“你想做什么?”
夏氏不允,恨恨看着罗婉:“你凭什么说我女儿害人?你有证据就拿出来!谁不知你恨我女儿恨得牙痒痒,现在看她不如意,又想来欺负她是不是?我看是你故意栽赃!”
罗婉面色无波,平静地说:“在三妹说出二妹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那花糕是二妹送的,如何栽赃?难不成母亲以为,我们是要栽赃三妹?”
“二妹为何不自己来送,不就是怕越郎有戒心,不会吃她的东西么?明日就是科举考试,一年一回,越郎为此已经埋头苦读三年,几乎是在书房闭关不出,难道越郎会为了栽赃二妹不惜再错过这个机会?”
罗婉看向安丰侯,“父亲,越郎的性子您是清楚的,他在圣上面前说过要考状元,您也看到了,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儿媳实在想不通,他何故要去栽赃二妹?再退一步,我们果真有意栽赃二妹,为何不拿着证据去报官,而是在这里做无谓辩解?”
安丰侯深觉罗婉句句在理,打算再叫人去抓宗孟芙过来。
夏氏却对罗婉道:“谁知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说不定是你想谋害元郎,你和姜家二郎私通的事,当我们都不知道吗!”